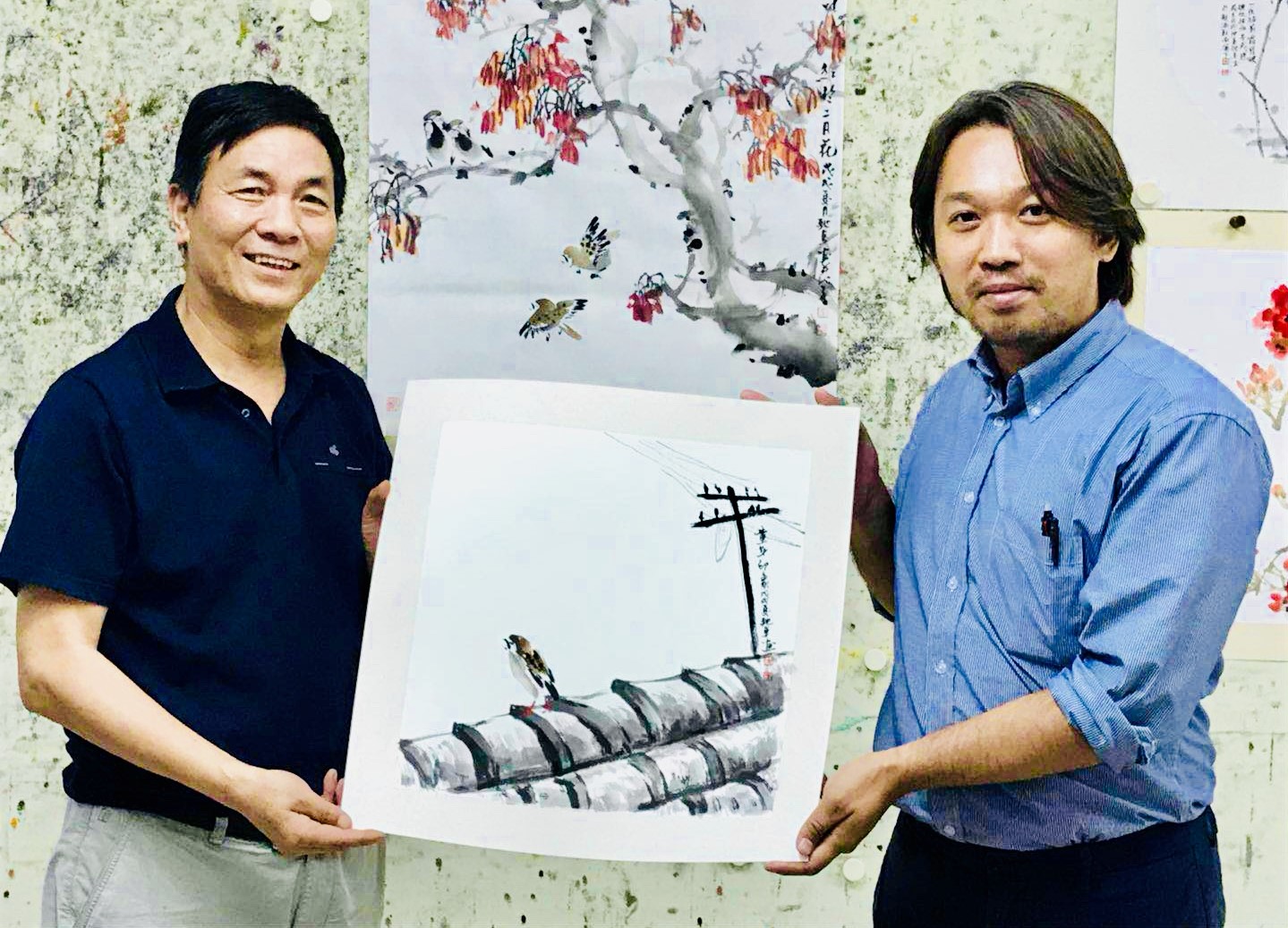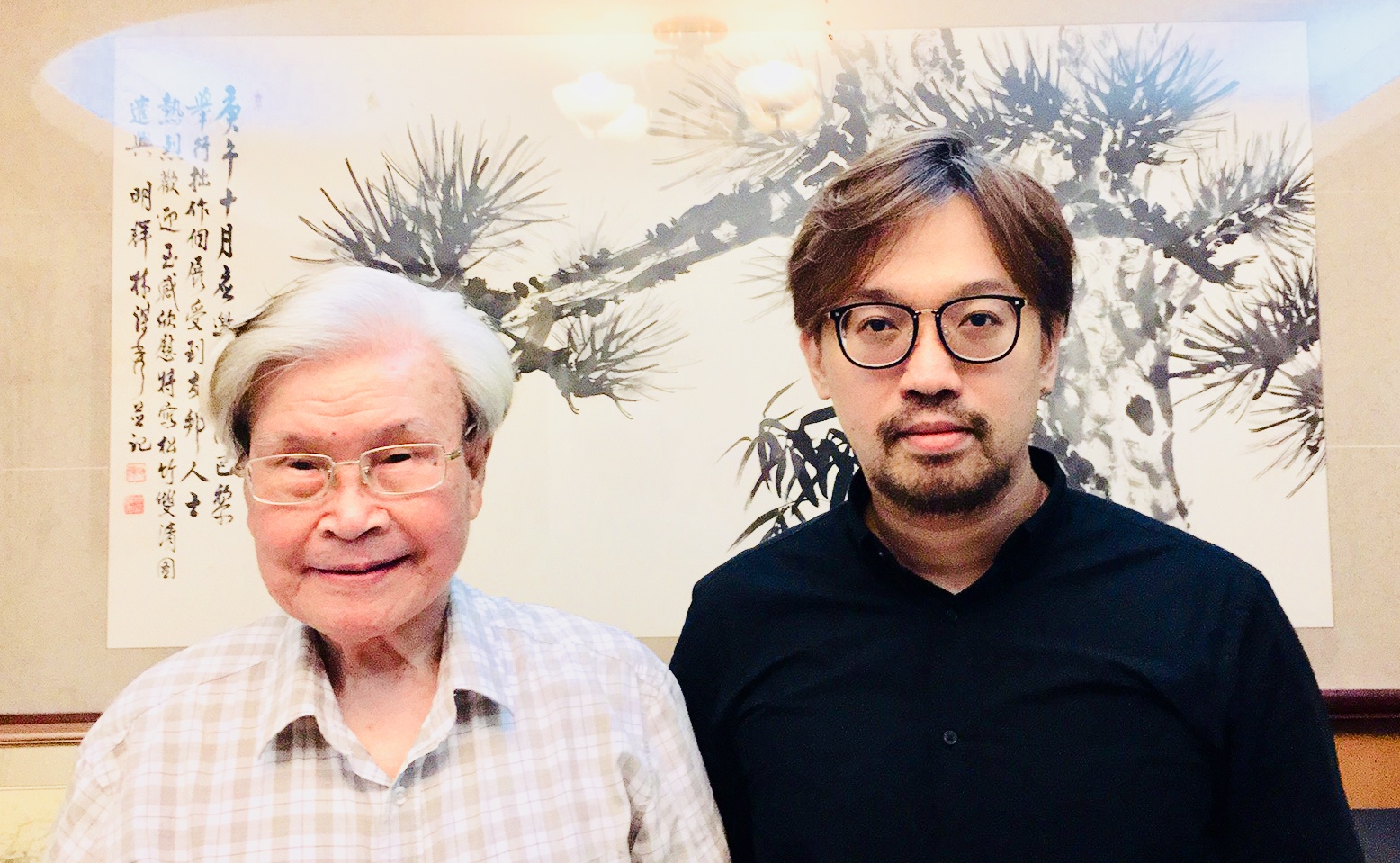台灣首位日本國立新美術館個展-王穆提續寫NAU前衛傳奇
文 / 國際藝術專題採訪組
歷史性的座標:台灣藝術家的日本國立新美術館突圍
2026 年初春,東京六本木。
當冬日的陽光穿透 國立新美術館(The National Art Center, Tokyo, NACT) 那標誌性的波浪狀玻璃帷幕,灑落在巨大的倒錐形混凝土柱上時,這座日本藝術的最高殿堂迎來了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在備受矚目的 《第24回 NAU21世紀美術連立展》 中,來自台灣的藝術家 王穆提(WANG MUTI) 獲邀參展。與一般參展者不同的是,他打破了大型公募展「單點展示」的慣例,獲得了 「獨立策展空間」 的特權。這標誌著他成為 「台灣首位」 在日本國立新美術館舉辦 「個展形式(Solo Exhibition within a Group Show)」 的藝術家。
這不僅僅是一次參展,這是一次 「文化主權的確立」。王穆提帶來的不是零散的畫作,而是三件高度逼近 4 公尺、構建完整世界觀的視覺鉅作——〈空中之色〉、〈聖境・阿里山〉、《中道之光》。他利用這些作品,在六本木的核心地帶,植入了一座屬於台灣當代藝術的「精神孤島」,與周遭數百件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品形成強烈對話。

場域的權力學 —— 對標世界頂級美術館
要理解「台灣首位」這個頭銜的含金量,我們不能僅將國立新美術館視為一個展覽場地,而必須將其置於 「世界美術館的權力光譜」 中進行對標分析。
國立新美術館是日本戰後美術館建築史上的奇點,由日本代謝派建築大師 黑川紀章(Kisho Kurokawa) 設計。它沒有永久館藏,專注於「展示」,這種 「空之容器(Empty Vessel)」 的特性,使其在國際上與以下頂級機構並列:
1. 法國巴黎大皇宮(Grand Palais):國家級的展示櫥窗
如同巴黎大皇宮是法國舉辦 FIAC 等頂級沙龍與國家特展的門面,國立新美術館是日本舉辦國際巡迴大展(如印象派大展、草間彌生回顧展)的首選之地。它代表了日本官方對藝術「最高規格」的定義。王穆提在此獲得個展空間,等同於在巴黎大皇宮的沙龍展中獲得獨立展位,象徵著其作品質感已達 「國家級規格」。
2. 英國皇家藝術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s):藝術家主導的殿堂
日本國立新美術館承擔著日本國內重要美術團體(如日展、二科展、NAU展)最高榮譽殿堂的責任。這與英國 RA 的「夏季展」邏輯一致——它是當代藝術家證明自己 「在場(On-site)」 的最高座標。對於亞洲藝術家而言,能在此佔有一席之地,意味著進入了日本主流藝術圈的核心視野。
3. 空間的極致挑戰:日本最頂級的國立美術館
日本國立新美術館擁有單一展廳 2,000 平方公尺的巨大尺度,天花板高度達 5 公尺。這種工業級別的空間,對藝術家是殘酷的考驗。如果作品的 「物理量感(Mass)」 或 「精神張力(Tension)」 不夠強大,瞬間就會被建築的氣場吞噬。
王穆提的成就,在於他帶來的作品高度皆逼近 400 公分。這種巨大的垂直量體,如同紀念碑一般,成功「鎮壓」住了這個流動的空間,將巨大的白盒子轉化為個人的道場。
前衛的系譜 —— 日本NAU的歷史靈魂
王穆提此次展出的另一重戰略意義,在於他所選擇的組織 —— NAU(New Artist Unit)。這不是一個普通的藝術團體,它是日本戰後前衛藝術精神的當代載體。
1960年代:新達達(Neo-Dada)的狂野源頭
NAU 的靈魂源頭,可追溯至 1960 年代後半震驚世界的 「新達達組織者(Neo-Dada Organizers)」。那是一個安保鬥爭與經濟起飛並存的躁動時代。
- 吉村益信(Masunobu Yoshimura): NAU 的精神教父,反藝術的領袖。他在 1960 年代將藝術從美術館拉入新宿街頭,策劃了激進的展演。
- 篠原有司男(Ushio Shinohara): 以「拳擊繪畫」聞名紐約的前衛狂人,代表了對「行動(Action)」的推崇。
2026年:從「破壞」到「連立」
經過半世紀的演變,吉村益信的「反藝術」精神轉化為今日 NAU 的核心哲學 —— 「連立(Renritsu)」。所謂「連立」,即獨立個體在保持異質性、不妥協個人風格的前提下,於同一時空中並肩而立。這是一個不再尋求統一風格,而是容納差異的「當代藝術公社」。
王穆提的歷史定位:智性的接力
作為 NAU 台灣首位成員,王穆提的加入標誌著這個前衛團體完成了「亞洲地緣政治」的重要拼圖。
他沒有選擇模仿日本的新達達形式(如破壞或行為藝術),而是帶入了他獨特的 「智性(Intellectuality)」。作為一位身兼 「數位美術館計畫主持人」 與 「當代佛教經論編輯者」 的雙重身分者,他用深厚的觀念架構與物質實驗,回應了 NAU 前輩荒川修作(Shusaku Arakawa)的「觀念藝術」遺產——藝術不是單一媒材的展示,而是思想的容器。
微觀視界 —— 三件鉅作的深度解讀
在國立新美術館展示室 1A,王穆提的三件作品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敘事閉環。這些作品全部完成於 2025 年底,展現了藝術家最新的創作爆發力。這三件作品皆為近 4 公尺高的巨幅創作,展現了極強的空間統攝力。
1. 〈空中之色〉—— 懸浮的重力與物質悖論
- 規格: 寬度 139 x 長度 390 cm
- 媒材: 宣紙、水墨、壓克力顏料
- 年代: 2025/12
- 這件高達 3.9 公尺的巨作,視覺衝擊力極強。畫面主體是一個巨大的、深黑色的團塊,彷彿是從地心深處挖出的岩石,又像是被燒焦的有機體 。然而,這個沈重的物體卻違背物理法則,懸浮在一個由壓克力顏料暈染出的、帶有粉紫色與淺藍色交織的背景中。
- 【深度藝評】
- 這是一場關於 「存在與虛無」 的辯證。王穆提利用水墨在宣紙上的滲透性,創造出黑色團塊沈重、粗糙的肌理,象徵著現實世界的 「重力」 與 「業力」。而背景則創造出輕盈、甚至帶有虛擬感的空性。這精準演繹了《大般若經》中「色不異空」的當代視覺版——最沈重的物質,其實漂浮在最輕盈的空性之中。
2. 《中道之光》—— 秩序的幾何與精神維度
- 規格: 寬度 138 x 長度 390 cm
- 媒材: 宣紙、水墨、壓克力顏料
- 年代: 2025/12
- 這是一件極具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風格的色域繪畫,但更具東方儀式感 。畫面被嚴謹地劃分為上、中、下三個區域。上下兩端是充滿物質躁動感、帶有金屬光澤的黑金色塊;中間則是一道橫亙的、平滑如鏡的紫白光帶。
- 【深度藝評】
- 這是三部曲的終章,直指東方哲學中的 「中道」 思想。上下的混亂(混沌)與中間的寧靜(秩序)在同一張宣紙上並存。王穆提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並沒有讓光帶「消除」黑暗,而是讓兩者 「共生」。這是一幅當代的祭壇畫,引導觀眾的視線從躁動的邊緣匯聚至中心的寧靜,進入一種冥想的狀態。
3. 〈聖境・阿里山〉—— 時間的拓片與崇高美學
- 規格: 寬度 142 x 長度 399 cm
- 媒材: 大畫仙紙(小津和紙出品)、水墨、壓克力顏料
- 年代: 2025/11/17
- 這件作品使用了極為特殊的 「小津和紙出品・大畫仙紙」,尺幅接近 4 公尺高 。全幅式(All-over)構圖被深邃的墨綠與灰黑佔據。那不是具象的樹葉,而是高度抽象化的肌理。幾道銳利的白色線條垂直貫穿,如同閃電穿透迷霧。
- 【深度藝評】
- 在藝術史語境中,這是一種 「崇高(Sublime)」 美學的展現。那些垂直的白色線條,既是樹的靈魂,也是連結天地的通道。這件作品證明了,透過當代媒材的轉譯,台灣的地景可以昇華為普世的精神圖騰。
- 王穆提拒絕了觀光客式的風景描繪,他直取阿里山神木的 「時間性」。大畫仙紙特有的纖維韌性,承受了顏料的反覆堆疊,形成了如同千年紅檜樹皮般的厚重質感。
從邊陲到中心的文化突圍
2026 年的東京六本木,因為王穆提的出現,多了一道來自台灣的光譜。他利用 國立新美術館 這個世界級的「大皇宮」,融入NAU21 這個承載了「新達達」歷史的前衛平台,成功地將台灣當代藝術的座標,從邊陲推向了中心。他證明了,一位台灣藝術家不需要模仿日本,也不需要迎合西方。只要誠實地挖掘腳下的土地(阿里山)、面對自身的文化(中道哲學),並具備駕馭巨大尺幅與跨媒材的能力,就能在世界藝術的最高殿堂,撐起一片屬於台灣的天空。
當雲端墜落於畫布:王穆提的「數位反動」與檔案式繪畫
—— 數位美術館主持人如何用近四米鉅作,抵抗演算法的虛無?
在國立新美術館展示室 1A 的王穆提個展現場,觀眾最直觀的感受是「重」。那是一種來自地質、來自歷史、來自物質本身的沈重感。
然而,這份沈重感背後隱藏著一個巨大的悖論:王穆提不僅是藝術家,更是一位資深的 「數位美術館計畫主持人」。他曾協助超過 2000 位藝術家建立數位資料庫,長期致力於藝術作品的數位化與雲端保存。
一位最懂「虛擬」的人,為何做出了最「實體」的作品?這正是解讀王穆提此次展出的關鍵鑰匙。
檔案意識(Archival Consciousness)—— 將繪畫視為儲存介質
在元宇宙、NFT 與 AI 生成藝術(AIGC)大行其道的今天,圖像(Image)變得前所未有的廉價。它們是平滑的、無厚度的、可被無限複製且隨時被刪除的像素集合。
作為數位專家,王穆提深知「數據」的脆弱性與「螢幕」的欺騙性。因此,他在創作中展現了一種強烈的 「檔案意識」。
拒絕平滑:對抗螢幕的觸感
他這次展出的三件作品,高度皆逼近 400 公分,媒材混用了東方的水墨與西方的壓克力顏料。這本質上是一種 「反數位」 的操作。
- 物理性的不可逆: 數位檔案可以隨時「復原(Undo)」,但水墨在宣紙上的滲透、壓克力顏料在畫仙紙上的堆疊,是不可逆的。王穆提利用這種不可逆性,在畫面上留下了無數次勞動的痕跡。
- 數據無法紀錄的細節: 站在 〈聖境・阿里山〉 面前,你會看到水墨與壓克力交融後產生的複雜微型地貌。這些細節是隨機的、有機的,是任何高解析度掃描儀或 3D 建模都無法完美還原的。他創造了 「唯有肉身在場(On-site)才能感知」 的震撼。這是對當代人習慣透過手機螢幕看畫的一種挑釁——你必須來到現場,因為螢幕無法傳遞這種物理量感。
策展人的畫筆:繪畫即備份
一般畫家畫的是「風景」,但作為策展人的王穆提,畫的是「關於風景的實體備份」。在 〈聖境・阿里山〉 中,他並沒有描繪阿里山的具象外觀,而是試圖複製神木的「質地」與「氣場」。那滿布畫面的深邃肌理,就像是他在畫布上建立了一個 「地質資料庫」。他試圖將那種崇高的精神性,封存進大畫仙紙的纖維之中,就像他將藝術作品封存進伺服器一樣。差別在於,伺服器保存的是冰冷的資訊,而畫布保存的是有溫度的 「靈光(Aura)」。
前衛的迴響 —— 從新達達的「反藝術」到王穆提的「反演算法」
王穆提此次參展的組織 NAU(New Artist Unit),其前身是 1960 年代的 「新達達(Neo-Dada)」。當年的吉村益信,用廢棄物與街頭展演來對抗傳統美學的僵化。而在 2026 年,王穆提繼承了這份前衛精神,但他對抗的對象變了。他不再對抗傳統油畫,而是對抗 「演算法的平庸化」。
身體性的回歸
NAU 的歷史強調「行動(Action)」。王穆提的創作過程充滿了極高強度的身體勞動。面對一張 4 公尺高的大紙,藝術家必須動用全身的肌肉來控制筆觸與顏料的流動。
在 〈空中之色〉 中,那個巨大的黑色團塊,其實是藝術家身體勞動的結晶。那是時間的沈積物,是人類意志強行介入物質世界的證明。這與 AI 生成圖像時「輕點滑鼠」的動作形成了鮮明對比。
連立的真義:在數據洪流中確立主體
NAU 標榜的 「連立(Renritsu)」,意指獨立個體的並存。在演算法試圖將人類審美同質化、大數據試圖預測我們喜好的時代,王穆提用這種極度個人化、極度手工感、極度巨大的實體作品,捍衛了藝術家的主體性。他證明了,即使在數位時代,人類手作的溫度、不完美與巨大的物理存在感,依然擁有無法被取代的神聖性。
三部曲的數位辯證 —— 重新閱讀視覺鉅作
當我們帶著「數位 vs. 實體」的視角,再次凝視王穆提的三件鉅作,會發現它們擁有了全新的解讀維度。
1. 〈空中之色〉:像素的黑洞
- 解讀: 畫面中央那個由水墨與壓克力堆疊而成的黑色團塊,可以被視為 「數據的黑洞」。它沈重、緻密,吸收了所有的光線與資訊。而背景那片粉紫色的漸層,則帶有強烈的 「數位霓虹(Digital Neon)」 質感,象徵著虛擬網絡的輕盈與空幻。
- 隱喻: 這幅畫展示了當代人的生存狀態——我們的肉身沈重地滯留在物理世界(黑岩),而精神卻漂浮在無重力的網路空間(粉紫背景)。
2. 〈聖境・阿里山〉:未被編碼的自然
- 解讀: 這是一幅拒絕被編碼的風景。王穆提運用了極其複雜的墨色與壓克力堆疊,創造出了一種 「高雜訊(High Noise)」 的視覺效果。這些雜訊不是錯誤,而是自然的本質。
- 隱喻: 在 AI 眼中,阿里山可能只是一組綠色的數據模型;但在王穆提筆下,它是充滿傷痕、歷史與不可預測性的有機體。這是對「自然」最深情的實體備份。
3. 《中道之光》:介面的昇華
- 解讀: 那道橫亙畫面的紫白光帶,像極了數位螢幕關閉前的那一道殘光,或是虛擬與現實的 「介面(Interface)」。
- 隱喻: 上下的黑金混亂代表了紛雜的資訊焦慮,而中間的光帶則是穿越資訊迷霧後的清明。王穆提在此提出了一種「數位時代的中道」:我們不應逃離科技,也不應沈溺於科技,而應在虛實之間,找到心靈的平衡點。
未完成的連立,永恆的主體:從台灣出發的文化突圍
—— 王穆提個展的文化政治學:在日本國立新美術館建立「台灣異托邦」
當我們從微觀的作品解讀,回到宏觀的文化視角,我們會發現王穆提(WANG MUTI)此次在國立新美術館的個展,具有超越藝術本身的文化政治意義。這不只是一位藝術家的成功,更是一個 「文化事件」。
在過去,亞洲當代藝術的論述往往由西方或東京主導,其他區域的藝術家常處於「被觀看」的邊陲位置。然而,王穆提此次的參展策略——以「個展規格」介入大型公募展——徹底翻轉了這個權力結構。他不再是尋求認可的參加者,而是帶著完整世界觀的 「對話者」。
地緣政治的審視 —— 拒絕邊陲,確立座標
王穆提選擇加入 NAU 並成為台灣首位成員,展現了極高的戰略眼光。他利用這次「展中個展」的特殊機制,在東京六本木建立了一個屬於台灣的文化主體座標。
台灣主體的在場
在過去,亞洲當代藝術的論述往往由西方或東京主導,台灣藝術家常處於「被觀看」的邊陲位置。但王穆提打破了這個框架。
- 巨大的物理存在: 他不只是掛幾張畫,而是用三件近 4 公尺的巨作,在物理空間上佔領了視線。這種 「紀念碑式(Monumental)」 的展示,本身就是一種強勢的宣言。
- 文化的自信: 透過 〈聖境・阿里山〉,他將台灣的地景記憶轉化為普世的精神體驗;透過 《中道之光》,他展示了東方哲學在當代抽象繪畫中的解釋權。
建立「異托邦(Heterotopia)」
法國哲學家福柯(Foucault)曾提出「異托邦」的概念,指在現實社會中構建一個真實卻又與眾不同的空間。王穆提在國立新美術館展示室 1A 建立的,正是一個 「台灣異托邦」。
- 在這個空間裡,〈聖境・阿里山〉 將台灣高山神木的崇高感與時間性,直接植入東京的都會中心。千年的水墨傳統與當代的壓克力媒材共生。這不是對日本風景的模仿,而是對台灣地景自信的展示。
- 〈空中之色〉 與 《中道之光》 則展示了台灣藝術家如何消化東方水墨與西方壓克力,創造出獨特的視覺語言。
他證明了,台灣藝術家只要挖掘自身文化的根源,並具備駕馭巨大尺幅與跨媒材的能力,就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不必成為誰的附庸。
NAU 的「連立」作為戰略支點
NAU 繼承了 1960 年代吉村益信「新達達」的反骨精神,其核心哲學 「連立(Renritsu)」 強調的是:沒有中心,只有節點;沒有階級,只有並存。王穆提不需要模仿日本主流的「膠彩畫(Nihonga)」或是迎合西方的「觀念藝術」。在 NAU 的連立架構下,他憑藉著三件高度逼近 4 公尺的鉅作,直接宣示了台灣藝術的 「在場(On-site)」。
策展型藝術家的回歸 —— 以「結構」抵抗「碎片」
在資訊碎片化的時代,王穆提給出的答案是:「結構」與「深度」。這也是他身為 「數位美術館計畫主持人」 給當代藝術界的一份答卷。
數位思維的實體轉譯
作為一位長期建置雲端資料庫的專家,王穆提深知「結構」的重要性。他在實體繪畫中,也展現了這種結構性的思考。
- 《中道之光》 的三段式構圖,就像是一個嚴謹的數據架構:上層的混沌(輸入)、下層的雜訊(干擾)、中層的光帶(核心運算與輸出)。
- 他將繪畫從單純的「感性抒發」,提升到了「理性架構」的層次。這是一種 「智性藝術(Intellectual Art)」,要求觀眾不僅是用眼睛看,更要用大腦去解碼。
抵抗演算法的平庸
面對 AI 生成圖像的氾濫,王穆提用 「巨大的物理量感」 進行抵抗。
演算法可以輕易生成一張完美的圖,但它無法生成一張 寬 142 公分、長 399 公分,且乘載了水墨滲透與壓克力堆疊厚度的 大畫仙紙。這種物理上的「不可複製性」,是王穆提對藝術靈光(Aura)的堅守。
未來的啟示 —— 新的前衛是「向內」的
回望 NAU 的歷史,從 1960 年代吉村益信在街頭的「向外爆發」,到 2026 年王穆提在美術館內的「向內凝視」,我們看到了一條前衛藝術演變的軌跡。
從破壞到建構
早期的前衛藝術旨在破壞舊有的美學秩序。而王穆提代表的新一代前衛,則是在數位廢墟之上進行 「精神的重建」。他不再憤怒地攻擊體制,而是溫柔而堅定地構建一個能夠安頓身心的精神空間。他利用國立新美術館這個「國家機器」,傳遞個人的、私密的、靈性的崇高體驗。
跨域的勝利
王穆提的成功,預示了 「跨域藝術家(Interdisciplinary Artist)」 的勝利。未來的藝術家,可能都必須像他一樣,同時具備 「數位專家的知識厚度」(如他的檔案意識)與 「實體藝術家的手感」(如他對水墨壓克力的掌控)。單純的視覺快感已不足以撼動人心,唯有思想的重量,才能在資訊洪流中站穩腳跟。
在日本國立新美術館中,尋找靈魂的錨點:王穆提的創作獨白
—— 專訪台灣首位國立新美術館個展藝術家:關於尺度、媒材與那些無法被數位化的「崇高」
對話 —— 為什麼必須是「四公尺」?
Q:在國立新美術館這樣巨大的場域中,您選擇了三件高度近 400 公分的鉅作。這是一個非常冒險的決定,請問背後的考量是什麼?
王穆提:「尺度(Scale)本身就是一種語言。國立新美術館的天花板高度超過 5 公尺,它是一個工業級別的『白盒子』。在這裡,普通的畫作會像郵票一樣被空間吞噬。作為台灣首位在此舉辦個展形式的成員,我不能只是『展示』,我必須『對抗』。
〈聖境・阿里山〉 的 399 公分高度,不是為了炫技,而是為了還原我在阿里山神木腳下感受到的那種『仰望感』。那種人類在自然面前的渺小與敬畏,只有透過這種紀念碑式的尺度(Monumental Scale),才能在東京的都會中心被重建。我要讓觀眾在走進展區的瞬間,身體被迫慢下來,視線被迫向上,這是物理空間對心理空間的干預。」
媒材的辯證 —— 水墨的「時間」與壓克力的「空間」
Q:這次的作品大量使用了「宣紙/大畫仙紙」結合「水墨與壓克力顏料」。這兩種媒材在屬性上幾乎是衝突的,您如何處理這種關係?
王穆提:「這正是我想要的衝突。我是數位時代的人,我們習慣了螢幕上 RGB 色光的和諧,但現實世界是充滿雜訊與衝突的。
- 水墨(Ink)是『時間』: 它在宣紙上滲透、暈染,那是不可逆的過程,代表了東方的流動性與歷史感。
- 壓克力(Acrylic)是『空間』: 它乾燥快、覆蓋力強,具有西方的物質感與現代性。
在 〈空中之色〉 中,我用水墨堆疊出那塊沈重的黑色岩石(業力),然後用帶有粉紫色霓虹感的壓克力顏料去包圍它、撞擊它。水墨的『滲透』與壓克力的『覆蓋』在同一張紙上博弈,這就像是我們當代人的處境——靈魂還停留在古老的傳統中,身體卻已被拋進了快速的數位現代性裡。」
身分的雙重性 —— 數位專家的「實體反擊」
Q:您也是一位資深的數位美術館計畫主持人,整日與虛擬數據為伍。這種背景如何影響您的實體創作?
王穆提:「正因為我太了解『虛擬』,所以我才更渴望『實體』。在數位資料庫裡,一張畫只是一個幾 MB 的檔案,它是平滑的、無厚度的。但在創作 《中道之光》 時,我能感受到宣紙纖維的阻力,能聞到墨與色混合的味道。這三件作品,其實是我對『演算法』的一種反擊。
AI 可以生成一張完美的圖,但它無法生成一張 寬 142 公分、長 399 公分,且乘載了無數次筆觸堆疊厚度的 大畫仙紙。這種物理上的『不可複製性』,就是藝術的『靈光(Aura)』。我希望觀眾來到六本木,不是來看一張圖,而是來體驗一個『場』,一個由物質、勞動與精神共同構建的實體場域。」
歷史的迴響 —— NAU21 與台灣的座標
Q:作為 NAU 台灣首位成員,您認為這次展出對於台日藝術交流有何意義?
王穆提:「NAU 的前身是 1960 年代的『新達達』,那是日本前衛藝術的黃金時代。能以台灣人的身分加入這個系譜,並獲得獨立策展空間,我認為這象徵著一種『平視』。
我們不再是單方面地接受日本或西方的美學標準,而是帶著台灣的 阿里山、帶著東方的 中道思想、帶著我們對數位時代的獨特反思,來到這裡進行對話。
我在國立新美術館建立的不是一個展位,而是一個 『台灣異托邦』。在這裡,文化沒有優劣,只有連立(Renritsu)與共生。我希望這三件作品能成為一個座標,證明台灣當代藝術有能力在世界級的殿堂中,發出屬於自己的、清晰而響亮的聲音。」
未來的預言
隨著 2026 年 2 月的個展落幕,王穆提在東京留下的不僅是三件鉅作,更是一個關於 「藝術如何回歸崇高」 的深刻提問。在這個萬物皆可 NFT 化、皆可 AI 生成的時代,王穆提選擇了一條最艱難的路:巨大的尺幅、難以控制的流動媒材、極高強度的身體勞動。他用 「數位專家」 的冷靜,洞悉了虛擬的極限;用 「前衛藝術家」 的熱情,擁抱了物質的溫度。這場在國立新美術館的個展,是王穆提藝術生涯的里程碑,也是台灣當代藝術走向國際核心舞台的一次重要突圍。正如他畫中那道穿越迷霧的 《中道之光》,這場展覽為迷茫的當代藝術,指引了一個關於「深度」與「真實」的方向。
紙上的建築學:解構王穆提四米鉅作的技術肌理
—— 台灣首位日本國立新美術館個展藝術家,如何以「小津和紙」與「壓克力」重塑當代水墨的物理性
在國立新美術館展示室 1A,當觀眾貼近王穆提的三件鉅作時,會驚訝地發現:遠看如碑的黑色團塊,近看卻充滿了無數微小的孔隙、流動與堆疊。這不是傳統水墨的「染」,也不是西方油畫的「塗」,而是一種全新的 「構造(Construction)」。
王穆提此次展出的核心技術成就,在於他成功地在 「極巨大的尺幅」 上,解決了 「異質媒材」 的衝突,並以此證明了台灣藝術家在當代媒材實驗上的高度成熟。
載體的意志 —— 當「小津和紙」遇見四公尺的野心
這次展出的一大亮點,是作品 〈聖境・阿里山〉 使用了日本頂級的 「小津和紙(Ozu Washi)出品・大畫仙紙」。
- 挑戰極限的載體:
- 一般的畫仙紙在超過 2 公尺後,對於水分的控制就變得極難掌握。而王穆提挑戰的是 399 公分 的極限長度。這種尺幅的紙張,本身就具有一種「建築性」。它不再只是繪畫的平面,而是一個巨大的、懸掛的「軟雕塑」。
- 文化的挪用與對話:
- 作為台灣藝術家,王穆提選用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傳統和紙,卻在上頭繪製台灣的阿里山神木,並使用西方的壓克力顏料進行覆蓋。這本身就是一種強勢的 「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 與對話。他利用日本和紙優異的纖維韌性(長纖維),去承受高強度的顏料堆疊,證明了「紙」也能展現出如同畫布(Canvas)般的厚重感,卻保留了紙張特有的「呼吸感」。
流動的戰場 —— 水墨與壓克力的「排斥美學」
王穆提作品中最迷人的細節,來自於 水墨(Water-based Ink) 與 壓克力顏料(Acrylic Pigment) 的交互作用。
- 親水 vs. 排水:在 〈空中之色〉 中,他先以濃墨在宣紙上進行底層的滲透,確立了黑色的深度(Depth)。待其半乾之際,直接撞入帶有膠質的壓克力顏料。
- 這時,油性的壓克力與水性的墨汁在纖維中發生了微觀的戰爭。壓克力排開了墨,墨又試圖滲透壓克力的邊緣。這種 「排斥作用(Repulsion)」 在畫面上留下了如同地殼變動般的裂痕與沈積紋理。這不是畫筆描繪出來的,而是 「物理與化學反應」 自動生成的自然地貌。
- 傳統水墨講求「相融」,但王穆提追求「排斥」。
- 當代的「破墨」:
- 這可以被視為中國傳統「破墨法」的當代激進版。王穆提用工業時代的產物(壓克力)去「破」農業時代的產物(水墨),創造出一種既古老又現代、既有機又合成的視覺語言。
身體的測量 —— 行動繪畫的東方演繹
在 NAU(New Artist Unit) 的歷史中,前輩篠原有司男以「拳擊繪畫」強調身體的介入。王穆提雖然沒有使用拳擊手套,但他面對 寬 142 x 長 399 cm 的畫紙時,其創作過程本身就是一場高強度的 「行動繪畫(Action Painting)」。
- 全身性的運筆:
- 要控制 4 公尺長線條的垂直度(如 〈聖境・阿里山〉 中的白色光束),藝術家不能只動手腕,必須動用全身的核心肌群,甚至需要在大尺度的畫面上不斷移動。
- 速度與控制:
- 壓克力顏料乾燥極快,水墨暈染又極不可控。王穆提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做出大膽的決策。這種 「速度感」 被封存在 《中道之光》 上下兩端的飛白筆觸中。那是藝術家身體能量的直接拓印,也是他在國立新美術館這個巨大空間中,確立「在場性」的物理證據。
技術即觀念
為什麼王穆提能成為 首位 在國立新美術館舉辦個展形式的台灣藝術家?
答案不僅在於他的哲學深度或文化論述,更在於他展現了 「駕馭巨大物質」 的技術能力。他將脆弱的紙張變成了堅固的碑,將衝突的顏料變成了和諧的場。這種對媒材的極致控制力,讓他有資格在這個亞洲最高等級的藝術殿堂中,不再是被動的參展者,而是主動的 「空間建構者」。透過這些 4 公尺高的鉅作,王穆提向世界展示了:台灣的當代水墨,已經超越了「文人畫」的案頭雅趣,進化為具有 「公共性」 與 「紀念碑性」 的強大藝術形式。
他是一位 「智性藝術家」,用學者的腦思考結構;他是一位 「數位策展人」,用檔案的意識保存靈光;他更是一位 「實體捍衛者」,用巨大的紙張與顏料,為這個日益虛擬化的世界,錨定了一個沈重而真實的物理座標。
這不僅是王穆提個人的勝利,更是台灣當代藝術在國際舞台上,一次自信而完美的 「在場(Presence)」。在國立新美術館展示室 1A,王穆提的展區給人一種強烈的 「向上仰望」 的身體感。三件鉅作——〈空中之色〉、〈聖境・阿里山〉、《中道之光》——皆呈現出極度狹長的垂直比例(高度約 390-399 cm,寬度約 140 cm)。
這種比例的選擇絕非偶然。在當代藝術中,橫向的寬銀幕(Landscape)通常代表敘事與風景,而縱向的直立(Portrait)則代表肖像與碑銘。王穆提選擇了後者,但他描繪的不是人,而是 「精神的肖像」。
垂直性(Verticality)作為一種抵抗
在數位媒體主導的今天,人類的視覺習慣被鎖定在 「水平滑動」(Instagram 的限時動態除外,大部分資訊流仍是橫向閱讀或短幅滾動)。
- 逆轉觀看權力:當觀眾站在 〈聖境・阿里山〉 面前時,視線無法一次捕捉全貌。必須先看見底部的沈重肌理(土地/根基),再緩緩向上移動,經過糾結的墨痕(歷史/時間),最後到達頂端穿透迷霧的白線(光/靈性)。
- 這個觀看過程本身,就是一場 「朝聖(Pilgrimage)」。王穆提利用物理尺度,讓觀眾在展場中重演了攀登阿里山的身體經驗。
- 王穆提的近四公尺高度鉅作,強迫觀眾的眼球必須進行 「大幅度的上下掃描」。
- 東方卷軸的當代轉譯:
- 這種狹長比例呼應了東方傳統的 「立軸(Hanging Scroll)」。但他放棄了傳統卷軸的留白與輕盈,改用 壓克力顏料 的厚重堆疊與 全幅式(All-over) 構圖,填滿了每一個角落。這是將「文人的私密卷軸」轉化為「公共的紀念碑」。
墨的現象學 —— 「黑」不是顏色,是空間
在王穆提的作品中,黑色(Black)佔據了統治地位。但他使用的「黑」具有雙重屬性:既有傳統松煙墨的「碳素感」,也有現代黑色壓克力的「塑膠感」。
- 吸光的黑洞:這與馬列維奇(Malevich)的《黑方塊》不同,王穆提的黑是有機的、會呼吸的。它象徵著 「物質的極致」 —— 所有的業力、記憶、歷史都沈澱於此。
- 在 〈空中之色〉 中,那個巨大的懸浮團塊並非平塗的黑。王穆提利用水墨在宣紙上的滲透性,創造了無數個微小的孔隙。這些孔隙會吸收展場的光線,使黑色呈現出一種 「無限後退的深度」。
- 物質的重量:
- 在 〈聖境・阿里山〉 中,墨色與深綠色壓克力交織,形成了如同千年神木樹皮般的厚重質感。這裡的黑不再是虛無,而是 「時間的重量」。它讓薄薄的畫仙紙,在視覺上擁有了如同鑄鐵或岩石般的量感。
數位霓虹(Digital Neon)—— 虛擬的誘惑
如果說「黑」代表了沈重的現實,那麼王穆提在背景處理上使用的「霓虹色系」,則直指當代的虛擬經驗。
- 人工的漸層:這種色彩是 「無機的」、「發光的」。它與前景那塊粗糙、吸光的黑色水墨團塊形成了劇烈的 「視覺矛盾」。
- 在 〈空中之色〉 的背景中,王穆提使用壓克力顏料創造出粉紫色(Magenta)與青藍色(Cyan)的柔和漸層。這種配色方案常見於 「賽博龐克(Cyberpunk)」 或數位介面的設計中。
- 符號的對撞:結局是: 那塊沈重的黑色岩石,尷尬而孤獨地懸浮在美麗卻虛幻的數位霓虹中。這精準地描繪了當代人的處境——我們肉身沈重,卻生活在一個輕盈的像素世界裡。
- 這是一種高明的修辭。藝術家並沒有批判數位時代,而是將「古老的水墨黑(前現代)」與「人造的霓虹光(後現代)」並置。
金屬與光 —— 世俗與神聖的介面
在三部曲的終章 《中道之光》 中,王穆提引入了第三種關鍵色彩:金屬色(Metallic)與白色。
- 躁動的金屬:
- 在畫面的上下兩端,他使用了帶有金屬光澤的金色與古銅色壓克力顏料。這些顏料會隨著觀眾的移動而反光,產生一種不穩定的、躁動的視覺效果。這象徵著 「世俗諦」 —— 充滿慾望、變動不居的物質世界。
- 絕對的白:在色彩心理學上,這種白象徵著 「淨化」 與 「秩序」。它切斷了上下兩端金屬色的躁動,建立了一個絕對理性的平衡點。這就是王穆提所謂的 「中道」 —— 在喧嘩的色彩中,留出一道白色的寂靜。
- 與之相對的,是中間那道橫亙的 「紫白光帶」。這裡的白色是平滑的、啞光的(Matte),它不反光,而是發出一種內在的靜謐感。
光影的共謀 —— 國立新美術館的場域加持
王穆提的這些色彩策略,在國立新美術館(NACT)特殊的展場環境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放大。
- 自然光的介入:
- NACT 的玻璃帷幕會引入自然光。在白天,陽光灑落在 〈聖境・阿里山〉 上,水墨的層次會變得極其豐富,彷彿看見了森林深處的苔蘚。
- 聚光燈的戲劇性:王穆提清楚地計算了 「光」 對 「媒材」 的影響。他不是在畫布上塗顏色,而是在 「調度光線」。他讓作品在不同的光環境下,展現出「物質(水墨)」與「幻象(壓克力)」的動態平衡。
- 到了傍晚,展場的人工聚光燈(Spotlight)亮起。這時,《中道之光》 中的金屬壓克力顏料會開始閃爍,而中間的白光帶顯得更加深邃。
新時代的視覺光譜
王穆提在東京六本木的色彩展演,打破了人們對「台灣藝術」或「水墨藝術」的刻板印象。他沒有停留在傳統水墨的「黑白灰」,也沒有迷失在西方抽象的「色彩爆炸」。相反地,他提煉出一種 「智性的色譜」:
用墨來錨定歷史的重量,用 霓虹 來隱喻數位的虛無,用金與白來辯證世俗與神聖。
這位台灣首位日本國立新美術館個展藝術家,用這三組色彩符號,為 2026 年的亞洲當代藝術,繪製了一張關於 「存在、虛擬與超越」 的哲學地圖。
- 藝術家: 王穆提 (WANG MUTI)
- 核心色譜:
- 實存黑 (Existential Black): 松煙墨+碳黑壓克力 —— 象徵物質、歷史、業力。
- 數位霓虹 (Digital Neon): 螢光粉紅、青藍漸層 —— 象徵虛擬、輕盈、幻象。
- 金屬與白 (Metallic & White): 金、古銅、鈦白 —— 象徵世俗慾望與神聖秩序。
- 展出作品: 〈空中之色〉、〈聖境・阿里山〉、《中道之光》
- 地點: 國立新美術館 展示室1A
流動時代的沈默定錨:王穆提個展的歷史判詞
—— 總結一位台灣藝術家,如何在國立新美術館留下「不可磨滅」的精神刻度
王穆提用 「策展人」 的宏觀視野佈局,用 「數位專家」 的敏銳度捕捉時代焦慮,最後用 「藝術家」 的雙手,完成了最原始、最艱難的實體抵抗。
物質的勝利 —— 對抗「輕」的時代
義大利文學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曾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中推崇「輕(Lightness)」。然而,在 2026 年這個資訊過載、影像氾濫的「超輕」時代,「重(Heaviness)」 反而成為了一種稀缺的品質。
王穆提的勝利,首先是 「物質的勝利」。
- 在一個萬物皆可雲端化的世界,他堅持搬運巨大的紙張、調和黏稠的壓克力、研磨黑色的松煙。
- 〈空中之色〉 那塊沈重的黑岩,就像是一個巨大的 「物理錨點」,狠狠地拋進了漂浮不定的數位海洋中。它告訴觀眾:真實是有重量的,記憶是有肌理的,崇高是需要仰望的。
跨域的融合 —— 「水墨壓克力」的新語言
在藝術史的長河中,東方水墨與西方油畫(或壓克力)長期處於對望甚至對抗的狀態。但王穆提在 近 4 公尺 的畫仙紙上,達成了一種 「不卑不亢的共生」。
- 拒絕二元對立:
- 他沒有讓水墨臣服於壓克力,也沒有讓壓克力模擬水墨。在 〈聖境・阿里山〉 中,水墨負責「滲透」與「時間」,壓克力負責「覆蓋」與「結構」。
- 台灣的混種美學:
- 這種混用(Hybridity)本身就是台灣文化的隱喻——海納百川,靈活轉化。他創造了一種既非傳統水墨、亦非西方抽象的新語言,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 「後數位時代的物質表現主義(Post-Digital Material Expressionism)」。
座標的確立 —— 台灣藝術的「在場」
最重要的一點,在於 「文化主體性」 的確立。王穆提作為 NAU 台灣首位成員,沒有選擇做一個安靜的旁觀者。他利用 國立新美術館 這個世界級的擴音器,大聲地講述了屬於台灣的故事。
- 《中道之光》 不僅是一幅畫,更是東方哲學在當代藝術語境中的一次強勢發言。它證明了,台灣藝術家有能力消化最艱深的哲學命題,並將其轉化為普世的、震懾人心的視覺形式。
王穆提在東京留下的這三座 「紙上的紀念碑」,其影響力才剛剛開始。他向世界證明了:
- 尺度(Scale) 是對抗平庸的武器。
- 物質(Material) 是靈魂最後的堡壘。
- 台灣(Taiwan) 是亞洲當代藝術不可忽視的發源地。
在這座巨大的「空之容器」——國立新美術館中,王穆提成功地植入了一個堅實的內核。這是一位來自台灣的修道者、策展人與藝術家,用他的智慧與汗水,為 21 世紀的藝術史,寫下的最精彩的一頁。
從「唯識」到「視覺」:王穆提鉅作背後的哲學引擎
—— 解析一位「學者型藝術家」,如何以中觀辯證法重構當代繪畫的空間
在國立新美術館展示室 1A,當觀眾凝視王穆提那三件近 4 公尺的鉅作時,往往會感受到一種超越視覺的「理性的冷靜」。這種冷靜,源自於藝術家深厚的佛學哲學背景。
不同於表現主義者依賴情緒的宣洩,王穆提的創作更像是一場 「哲學的演繹」。他將畫布視為論證的場所,將顏料視為辯證的詞彙。要真正看懂這些作品,我們必須借用他長年鑽研的兩把思想鑰匙:唯識學(Consciousness-Only) 與 中觀學(Madhyamaka)。
唯識學的當代轉譯 —— 數位時代的「萬法唯識」
王穆提身為 數位美術館計畫主持人,整日處理虛擬影像與數據。這與他鑽研的 「唯識學」 產生了奇妙的共振。唯識學主張「萬法唯識」,即外部世界其實是心識的變現。
- 〈空中之色〉的「相分」與「見分」:
- 在作品 〈空中之色〉 中,那塊懸浮的黑色團塊,象徵著唯識學中的 「相分(Object)」 —— 即被我們感官所執著的物質對象。而背景那片帶有數位霓虹感的粉紫漸層,則象徵著 「見分(Subject)」 —— 即帶有主觀色彩的認知投射。
- 哲學解碼:
- 王穆提利用 水墨的沈重(實體) 與 壓克力的輕盈(虛擬),在畫面上演繹了這場「心」與「境」的對立。他告訴觀眾:在數位時代,我們所看到的「真實」,往往只是演算法與屏幕投射出的「幻相(Virtual Reality)」。這幅畫是對「數位唯識觀」的視覺批判。
中觀學的空間辯證 —— 破除二元對立
如果說唯識學解釋了「虛擬」,那麼 「中觀學」 則解決了「對立」。中觀學派的核心是龍樹菩薩的「八不中道」,旨在打破「有/無」、「生/滅」的二元執著。
- 《中道之光》的「二諦」結構:
- 作品 《中道之光》 的三段式結構,完美對應了中觀學的 「二諦(Two Truths)」 理論。
- 上下兩端的黑金躁動: 對應 「世俗諦(Conventional Truth)」,充滿了現象界的混亂、慾望與物質性。
- 中間的紫白光帶: 對應 「勝義諦(Ultimate Truth)」,象徵著超越語言與現象的空性。
- 哲學解碼:
- 王穆提的高明之處在於,他讓這兩者在同一張宣紙上 「並存」。中間的光帶並沒有消除上下的黑暗,而是與之共生。這視覺化了「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的深奧教義。他用 壓克力顏料 的平滑質感(光帶)去切斷 水墨 的混沌肌理(黑金),在形式上達成了一種 「視覺的中道」。
崇高的現象學 —— 從「觀想」到「觀看」
在佛教修行中,「觀想(Visualization)」 是一種透過心靈構建聖境的修持。王穆提將這種內在的觀想,外化為 4 公尺高 的實體繪畫。
- 〈聖境・阿里山〉的「依正不二」:那滿布畫面的神木肌理,既是阿里山的客觀風景(依報),也是藝術家內在精神的投射(正報)。透過 大畫仙紙 的巨大尺幅,他邀請觀眾進入這個「依正融合」的場域。
- 在 〈聖境・阿里山〉 中,他運用了天台宗 「依正不二」(主體與環境不二)的概念。
- 哲學解碼:
- 當觀眾仰望這件作品時,他們不僅是在看畫,而是在進行一場 「視覺的止觀」。那些垂直的線條引導視線向上,幫助觀眾從日常的瑣碎中抽離,進入一種崇高的精神狀態。
智性的重量
在當代藝術圈,充斥著大量的圖像消費與淺薄的觀念挪用。王穆提的出現,顯得尤為珍貴。他證明了,一位藝術家可以同時是 「數位專家」 與 「佛學行者」。他用 「唯識」 解析了數位虛擬的本質,用 「中道」 平衡了水墨與壓克力的媒材衝突。
他在國立新美術館留下的,不只是三件巨大的畫作,而是一套完整的 「視覺哲學體系」。這也是為什麼他能以 台灣首位的身份,在這個亞洲最高藝術殿堂中,獲得學術界與評論界高度評價的根本原因——因為他的作品,擁有思想的重量。
【展覽學術關鍵字 Recap】
- 哲學體系: 唯識學 (Yogacara)、中觀學 (Madhyamaka)、天台止觀
- 核心概念:
- 相分/見分: 對應 〈空中之色〉 的黑岩與背景
- 二諦 (世俗/勝義): 對應 《中道之光》 的上下黑金與中間光帶
- 依正不二: 對應 〈聖境・阿里山〉 的主客融合
- 展出藝術家: 王穆提 (WANG MUTI)
- 展出地點: 國立新美術館 展示室1A
從「參展者」到「定義者」:王穆提留下的戰略藍圖
—— 後展覽時代的觀察:數位文人的崛起與台日藝術交流的新典範
隨著 2026 年 2 月 15 日展覽落幕,國立新美術館展示室 1A 回復了平靜。然而,王穆提(WANG MUTI)此次的行動,在策展與文化戰略層面上,激起了長久的漣漪。
他打破了過去台灣藝術家在國際公募展中「單打獨鬥、淹沒於群體」的宿命,透過 「巨大的物理尺度」 與 「深厚的哲學論述」,成功將一個聯展攤位,轉化為一座獨立的 「微型美術館」。
戰略典範 —— 「展中個展」的微型權力學
王穆提此次最值得後進學習的,是他的 「空間權力學」。
- 微型美術館的建構:他利用作品本身作為「牆體」,在開放的空間中切出了一個私密的、高密度的精神空間。這使得他在 NAU 的展覽中,實際上擁有了一個獨立的 「個展權力」。
- 在大型聯展(Group Show)中,藝術家通常只能分配到牆面的一角。但王穆提透過 三件近 4 公尺 的鉅作,構建了一個 ㄇ字型的封閉場域。
- 啟示:
- 這告訴未來的參展者:不要只是去掛畫,要去 「造境」。在國際舞台上,唯有建立起自己的「空間主權」,才能在數百件作品中脫穎而出。
身分典範 —— 「數位文人(Digital Literati)」的誕生
王穆提的雙重身分——數位美術館計畫主持人 與 當代藝術家——定義了一種全新的藝術家型態:「數位文人」。
- 古代文人的當代轉世:
- 古代文人(Literati)是「學者」與「畫家」的結合,他們畫畫是為了載道。王穆提繼承了這一點,但他載的「道」經過了數位時代的濾鏡。
- 技術與思想的雙核驅動:這種 「左腦(數位/邏輯)」 與 「右腦(水墨/靈性)」 的完美結合,讓他能夠創作出既有當代視覺衝擊力,又經得起哲學推敲的作品。他證明了,未來的藝術大師,必須是技術與思想的 「雙重專家」。
- 他一方面擁有 建置資料庫 的理性邏輯(結構嚴謹、檔案意識),另一方面擁有佛學經論 的感性深度(中道思想、崇高美學)。
美學典範 —— 台灣作為「媒材煉金術」的實驗場
此次展出的 〈聖境・阿里山〉 與 《中道之光》,展示了台灣藝術家在媒材實驗上的靈活性。
- 混種的勝利:這種 「混種(Hybridity)」 正是台灣文化的優勢。他向日本觀眾展示:水墨可以很厚重(像油畫),壓克力可以很空靈(像水墨)。這種對媒材的 「誤讀」 與 「重構」,正是創新的源頭。
- 日本畫壇往往壁壘分明(日本畫 vs. 洋畫),但王穆提打破了界線。他將 小津和紙(日本)、松煙墨(東方) 與 壓克力顏料(西方) 放入同一個熔爐中。
至此,我們完成了對 王穆提國立新美術館個展 的全方位解讀。從場域的榮耀、技術的細節、哲學的深度,到未來的戰略意義。在這個轉折點上,我們看見一位來自台灣的藝術家,拒絕了數位的虛無,擁抱了物質的重量;拒絕了邊陲的沈默,發出了主體的聲音。
王穆提在六本木留下的,是三幅畫,也是三個預言:
- 實體將比虛擬更昂貴。
- 哲學將比圖像更迷人。
- 台灣將在世界藝術版圖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不可替代的座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