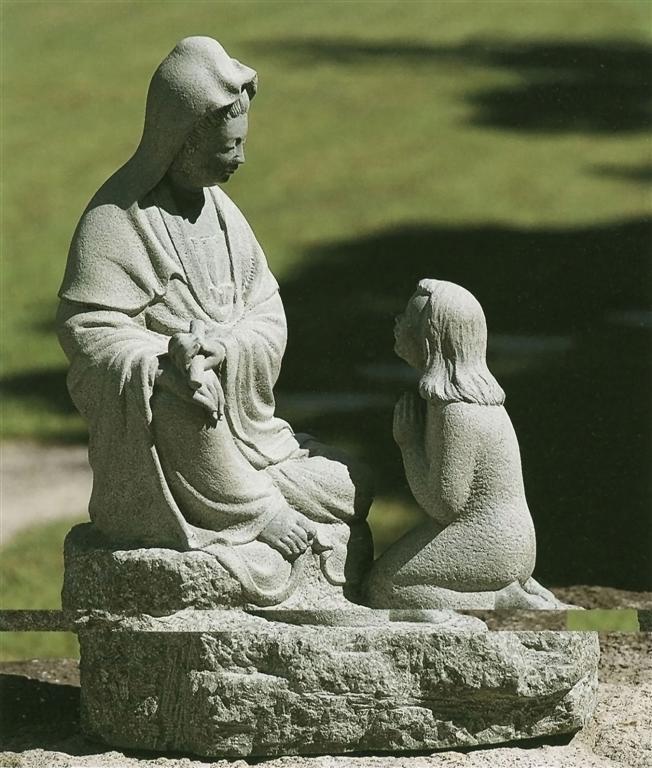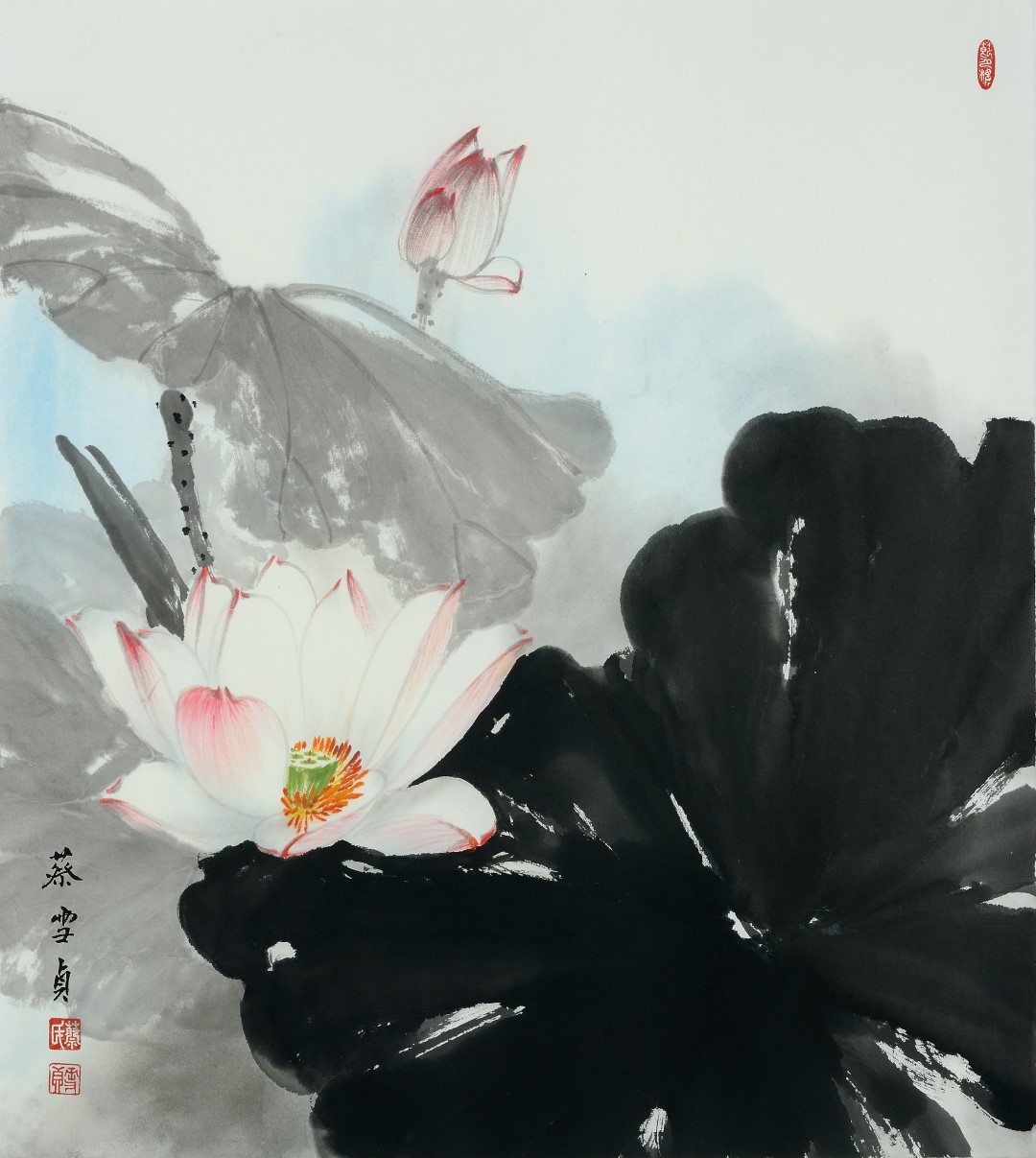中元節本為住民以豐收土地而感念大地所發,爾後轉變為祭祀天、地、水三位一體之地官,源於漢、始於《儀禮·覲禮》,後又與巫覡宗教合流。如袁桷《燔柴泰壇議》提及:「《祭法》亦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此中即取自《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
佛教盂蘭盆(Ullambana)節本為供養聖僧之義,爾後融入施餓鬼、祭祖之途,與印度祖先節相類。日本則由平安僧空也之踴念佛為始,經由一遍而發展至如今各地盆踊。然盂蘭盆節真義當為修持回向彼等所受苦之往昔父母等有情,由供養聖僧所得果而令彼等入餓鬼趣等有情離苦得樂,其實應當稱為「僧寶節」較為妥當。《說無垢稱經》云:「若有施主以平等心施此會中最下乞人,猶如如來福田之想——無所分別,其心平等,大慈大悲——普施一切不求果報,是名圓滿法施祠祀。」
《瑜伽燄口》其實在中國大明時就有稱為「瑜伽教僧」專門負責此類法會活動之執事者,輾轉傳入台灣之後,諸多佛教、民間信仰等廟宇也早已習慣每年盂蘭盆節多少會實施《瑜伽燄口》施餓鬼等。早期活動結束之後,各種供品用火燒之,如今則讓信徒自行攜帶回家,以求環保,同一期間,台灣約莫有一萬數千餘座民間信仰廟宇,大部分都會實施《瑜伽燄口》。台灣儀式僧源於大明之「瑜伽教僧」與大清之「應赴僧」,而雲南大理古國之阿吒力教實際上源於大明之「瑜伽教僧」(科儀等儀軌),此前,大元則稱為「阿拶哩」,意義類同。如《雲南阿吒力教經典及其在中國佛教研究中的價值》中云:「「教」傳入雲南後,為了能迅速發展,教僧就替自己在雲南歷史上尋找依據。元代及其以前稱僧人為「阿左梨」,為了與之掛鉤,教僧就擬出一系列音近的詞——阿吒力、啊吒力、阿拶哩等。他們還根據當時雲南流行一些說法,編造自己的歷史。由於明初《白古通記》將大理說成就是印度,是妙香佛國,大理土著有印度血統,於是就有教僧稱:「夫西竺有姓名曰阿拶哩,是毗盧遮耶族,姓婆羅門,從梵天口中而生,教習秘密大道。」」此中,法相唯識宗之《瑜伽》所言瑜伽師與此定義並不相同,如《瑜伽釋》云:「三乘行者、由聞思等次第習行如是瑜伽,隨分滿足,展轉調化諸有情故;名瑜伽師。或諸如來、證瑜伽滿。隨其所應,持此瑜伽、調化一切聖弟子等,令其次第修正行故;名瑜伽師。」
台灣原住民如西拉雅族「夜祭」即於Kuva中對Alid唱向、說向、唸咒以求感恩祈福。另外據台灣原民會記錄諸如:泰雅與太魯閣族的「祖靈祭」、邵族的「新年祭」、賽夏族的「矮靈祭」、布農族的「射耳祭」、鄒族的「戰祭」、沙阿魯阿族的「貝神祭」、排灣族的「五年祭」、魯凱族的「小米收穫祭」、阿美族的「海祭」與「豐年祭」、卑南族的「猴祭」與「大獵祭」、達悟族的「飛魚祭」與「新船下水祭」大抵亦為對祖靈感恩之祭典。
如今若作為文化傳承看待,也是較能直觀人類文化發展過程中之經驗累積而有多重文化之結果。
(台灣新北市頂泰山巖內之顯應祖師,相傳該像已經有八百餘年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