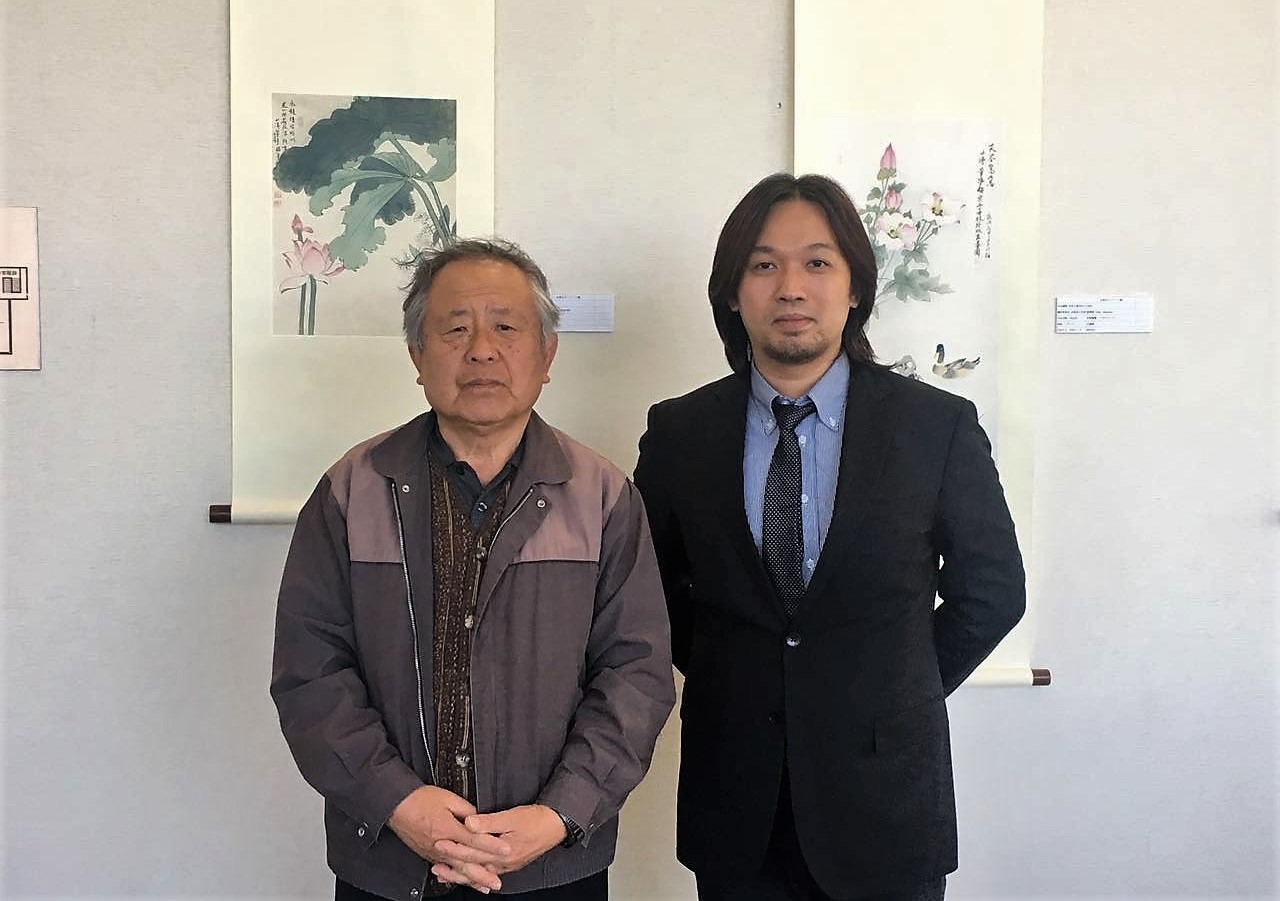阿彌陀佛。
慶X法師:
一、奘師所翻經論只要仔細閱讀、細細思維,即知其翻譯以四字一句模式乃屬漢語功力甚好之境界,能令學人更亦受用。是故,前言要自行先訓讀、疏文、斷句等之義亦在於此,只有學人自行深入方能了會於心。
二、《成唯識論》〈疏文斷句四字版〉:
「復次,生死相續,由諸習氣,然諸習氣,總有三種:
一、名言習氣,
謂有為法,『各別』親種。
名言有二:
一、表義名言,
即能詮義,音聲差別;
二、顯境名言,
即能了境,心、心所法。
隨二名言,
所熏成種,作有為法,各別因緣。」
既為各別親種、各別因緣,如何能為「表義也是在顯境之上安立」?
基師《述記》又言:「一切熏種,皆由心、心所,心、心所熏種,有因外緣,有不依外。不依外者,名顯境名,若依外者,名表義名,以分二別。然名自體不能熏種。」即知功能不同。
三、若按《攝論釋》:「欲顯虛妄分別但以依他性為體相。亂識及亂識變異,即是虛妄分別。分別即是亂識,虛妄即是亂識變異。」
四、《成唯識論》〈疏文斷句四字版〉:「想,謂於境,取像為性,施設種種,名言為業。謂要安立,境分齊相,方能隨起,種種名言。」苦、樂等當為受,而非想所攝之名言,二者不同。由取青黃等相,便起名言。五遍行者何?思之。
五、大論並無計度分別等名相。原意應當為《瑜伽》言:「自性分別,若差別分別,若總執分別」是為大論三分別,而後又開說「能生分別戲論所依、分別戲論所緣事,謂色等想事為依緣故,名想言說所攝、名想言說所顯分別戲論,即於此事分別計度非一眾多品類差別;...。」計度者,乃於自性、差別、總執分別,故言「即於此事分別計度非一眾多品類差別」。「云何名為自性分別?謂於一切色等想事,分別色等種種自性所有尋思,如是名為自性分別。」若言「計度分別」者,按《成唯識論》:「三分別中,計度分別能為七中有相分別乃至『不染』,非『五』、「八識』有此能故。」
六、《成唯識論》舉「隨念、計度」分別,乃證第七識為意識所依,而非尋伺等義。
七、基師言:「問︰自性分別,《攝論》說云五識中有,《對法》第二說自性是有相,有相即「尋」、「伺」,故知有相在於五識,亦非意不共,如何別也?
答︰彼《攝論》者,隨順理門說在五識,以五識中無「尋」、「伺」故,《對法》說言自性分別是有相收,非任運攝,故知五識無自性分別。
又解︰五識亦有,以《攝論》為正。
自性分別亦有二種:
一即是五識,二是「意識」相應「尋」、「伺」。
「意識」相應「尋」、「伺」故,《對法》說自性是有相,有相是意不共業,自性不是任運所收。
以五識故,說五識有自性分別,是非「尋」、「伺」,亦無過也。」
八、《瑜伽》依瑜伽行而分前八識、四禪修證而依有尋有伺地至無心地,此論首重者何?止觀故。五識身相應地卷首即說,兩百卷《婆沙》以「世第一法」為開頭,不知所問為何?最好還是依漢語經論為主。
九、(一)、《四部宗義》(日本亦有類似此等名稱之論書,只不過按天台等宗判別)早期皆稱《宗義寶鬘》(貢卻亟美汪波 著),本人版本應當為幾十年以前的,所以不知法師版本為何,應當為《四宗要義講記 》,然《四部宗義》與《四宗要義講記 》畢竟為二書,如《攝論》、《攝論釋》。
(二)、以下僅就本人所藏版本說明:
「四諦的差別法─無常等十六行相、常一自在之我空,是粗品的人無我。獨立自主我空,是細品的人無我。」
(三)、「獨立自取」者,應當出自《修心日光論》,而非《四部宗義》,如說:「太狹者,即雖然認許薄伽梵教說的四法印為如實語是所有內道一致共許的見解,但是當確認所謂『諸法無我』的所無之我時,諸聲聞部即不作法我以及遮彼的法無我的建立;所謂無我的歸攝之義,唯指手甫特伽羅無我,而且也認許唯空了補特伽羅獨立自取實體有」
(四)、「二取異體」者,語出《善顯》,如說:「由是獨覺亦有通達真實義者,非獨覺定不能斷內心上之實執。即聲聞乘,亦須分通達不通達真實義之二。現觀莊嚴論亦說小乘為二類,故執二取異體之實執。是否安立為所知障,亦應分二類也。」
(五)、「自相成就」者,語出《四宗要義講記 》,如說:「『唯識師說:非唯由分別假立,其由自體成就者(有自體者),為自相有、自相成就、勝義諦。其唯由分別假立之法,則與上相違。依他起與圓成實為前者,遍計執為後者也』。 」唯識並無此說,然依基師《義林》所謂「分別假立」者,乃「此要散心分別假立,是比量境;一切定心離此分別,皆名現量。」「自相成就」者,依登地 無著菩薩《顯揚》義,乃在於對「去來實有論」執取於過、未法有其自相,謬計為實有,如菩薩言:「去來實有論者,謂如有一,若沙門,若婆羅門,或在此法,由不正思惟,起如是見,立如是論:有過去,有未來,自相成就,猶如現在,實有非假。」
(六)、「假設一法,它縱然有個自相,但那個自相毫無所以自成之力而只是由一『分別假立』(內心安立)的,如果抽去分別假立的部分,那個自相就完全沒有了的話,這就是世俗諦、是共相、是非自相成就。假設另有一法,它的所以存在,不靠分別假立,即除了名言安立之外,它自已實有所以成立的根據,這就是勝義諦、是自相有、是自相成就。依、圓二性是『實有唯事』(『唯』字簡除『分別假立』),故是勝義有,遍計所執是『唯假立事』(『唯』字簡除『自立之相』),故是世俗有。」
然《瑜伽》言:「問:若一切法自相成就,各自安立己法性中,復何因緣建立二種所成義耶?
答:為欲令他生信解故,非為生成諸法性相。」二者意義並不相同,是信彌勒所言,或法尊師說?
又「唯」字者,《述記》:「唯,謂簡別,遮無外境;識,謂能了,詮有內心。識體即唯,持業釋也。」乃為簡別義,而非簡除分別假立,乃為簡別遮止無有外境之義,兩者意義差異頗鉅。
《四宗要義講記 》所言乃現代人所翻譯,翻譯與漢語唯識所說不同、內容差異極大,不可不慎,若有相同者,還望以古德所翻為準。
十、(一)、《成唯識論》〈疏文斷句四字版〉:「然諸我執,略有二種:
一者、俱生;
二者、分別。
俱生我執,
無始時來,虛妄熏習,內因力故,恒與身俱,不待邪教,及邪分別,任運而轉,故名俱生。
此復二種:
一、常相續,
在第七識,
緣第八識,起自心相,執為實我;
二、有間斷,
在第六識,
緣識所變,五取蘊相,或總或別,起自心相,執為實我。
此二我執,
細故難斷,後修道中,數數修習,勝生空觀,方能除滅。」
(二)、呈上論云:「生死相續,由惑、業、苦。
發業潤生,
煩惱名惑,能感後有,諸業名業,業所引生,眾苦名苦。」以上二者即表示,發業潤生與俱生我執並不能說為直接關係,譬如言嬰兒一出生即執我,然是否發潤惡業?於此觀之即知彼說很有問題。又或法師見到血即會頭暈,此即俱生我執,然是否能直接潤發惡業?當然否。
又,《義林》言:「心所相應者,第七識中俱生我見,《成唯識》第四卷有說:心所唯九法俱,謂遍行五、我癡、我見、我慢、我愛。」如說我愛,於俗事時,因為有我愛,故有欲界種種世俗善法滋生,如家庭等組成,然是否發潤惡業?當然亦否。又,常人於高空彈跳、登高山等,畏懼此色身我消失、死亡,是否發潤惡業?當然亦否,世俗等理即知。然大論言:「『一切煩惱皆能續生』,即是『發業潤生』煩惱。」唯「煩惱障」能「發業潤生」,又「煩惱障」以我執為根,因有我執,生諸煩惱。
十一、無漏種、薰習義、佛性義,可再詳閱《能顯中邊慧日論》。或參閱:https://www.cittamatrin.com/index.php/reasons-for-buddhahood
十二、《俱舍》言:「福有二類:
一捨、
二受。
捨類福者,謂由善心但捨資財施福便起。
受類福者,謂所施田受用施物施福方起。」
此中所譬似乎與「嗔打菩薩」不同。又如瞋打婦人,得偷蘭遮。大論言無間同分者:「謂如有一,於阿羅漢尼及於母所行穢染行;打最後有菩薩;或於天廟、衢路、市肆立煞羊法,流行不絕;或於寄託、得極委重、親友、同心、耆舊等所,損害欺誑;或於有苦、貧窮、困乏、無依、無怙為作歸依,施無畏已,後返加害,或復逼惱;或劫奪僧門;或破壞靈廟。如是等業,名無間同分。」
若按《論記》:「 『無間業同分』者,謂無間業同類之罪。
基云:「汙阿羅漢尼及母」,是害母類;
「打最後有菩薩」,是殺父類;
「或於天廟等行殺,或於委重所損害,或於貧、苦、困施無畏已,返害逼惱」,是殺阿羅漢類;
「劫奪僧物」,是破僧類;
「破壞靈廟」,是出佛身血類。或總稱類,不須別配。
今解:染無學尼是殺阿羅漢類,染母是殺母類,打最後有菩薩及破壞靈廟是出佛血類,劫奪僧門是破僧類,餘是殺父等類。」此等即知非「瞋打菩薩」即得無間業同分,於世俗「貧、苦、困施無畏已,返害逼惱等,」等同造無間業同分,並不僅只於瞋打菩薩等事爾,此中亦可會通《婆沙》言證阿羅漢果之前,於螞蟻之子亦不殺。
十三、《法華》常不輕菩薩於未證果之前,亦常於大眾之前說法,亦令人追打等事,是否菩薩讓彼等違背律儀等事?非也。於未來事等皆為彼菩薩所攝受眾也。應當隨分隨力分享佛法與世俗人才對,特別是於此惡世間,若無佛法薰染,異生造惡之可能更大,此等即於「左翼佛教」或者說「社會型佛教」所思考之事,如說慈悲,而於現實生活所見有情卻無有感受等事,如何說慈悲?不如觀想彼等有情若於我所違背諸多律儀,一切惡業皆當我替其承受而生大悲。
十四、《法界安立圖》作者 仁潮法師,彼處於明國最為黑暗之時代,萬曆年間,四大高僧被處死、折磨等事,其著名居士亦受死等折磨之災,故或者以他力信仰如淨土真宗等說而期盼於此穢土得以往生淨土,明末僅只淨土、天台、禪宗持續至今,當時又得賴於陽明學者傳至台灣、日本,如黃檗宗等。
十五、杭州續法師《賢首五教斷證三覺揀濫圖》甚好。
十六、每個佛寺、僧團規定皆不同。如早年渡海來台專宏淨土之廣欽老和尚(已經往生)所在之新北市土城區承天禪寺,一出家者不論學經歷,一律先做苦役,如洗菜、洗衣服等事。又如佛光山出家僧眾,每位出家僧眾似乎皆有自己固定之寮房,同學之間亦不准進入對方之寮房。又如日本曹洞宗總持寺凌晨三、四點即起來坐禪。又如台灣嘉義巴利語佛教每週固定經行托缽於市區街道上。於此種種,各自不同。
以上礙於時間,僅能略說,望祈海涵。
(圖片說明:日本京都大日如來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