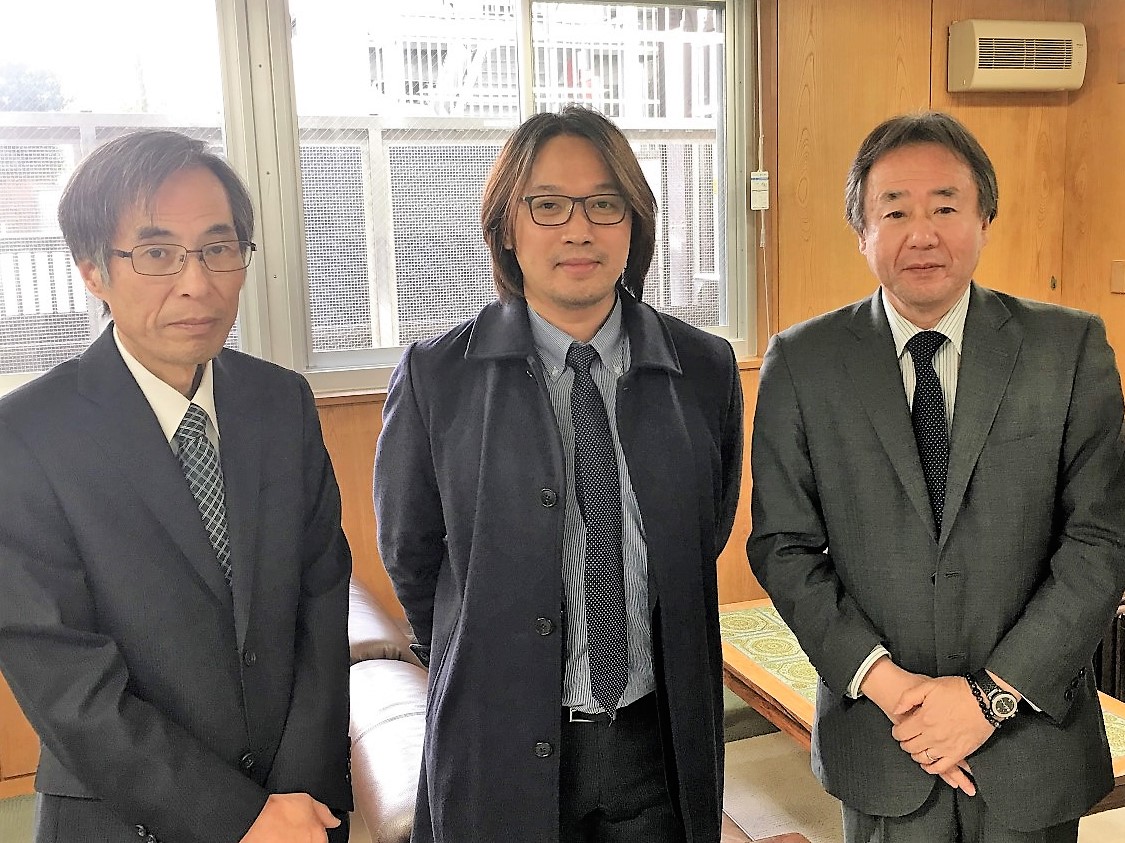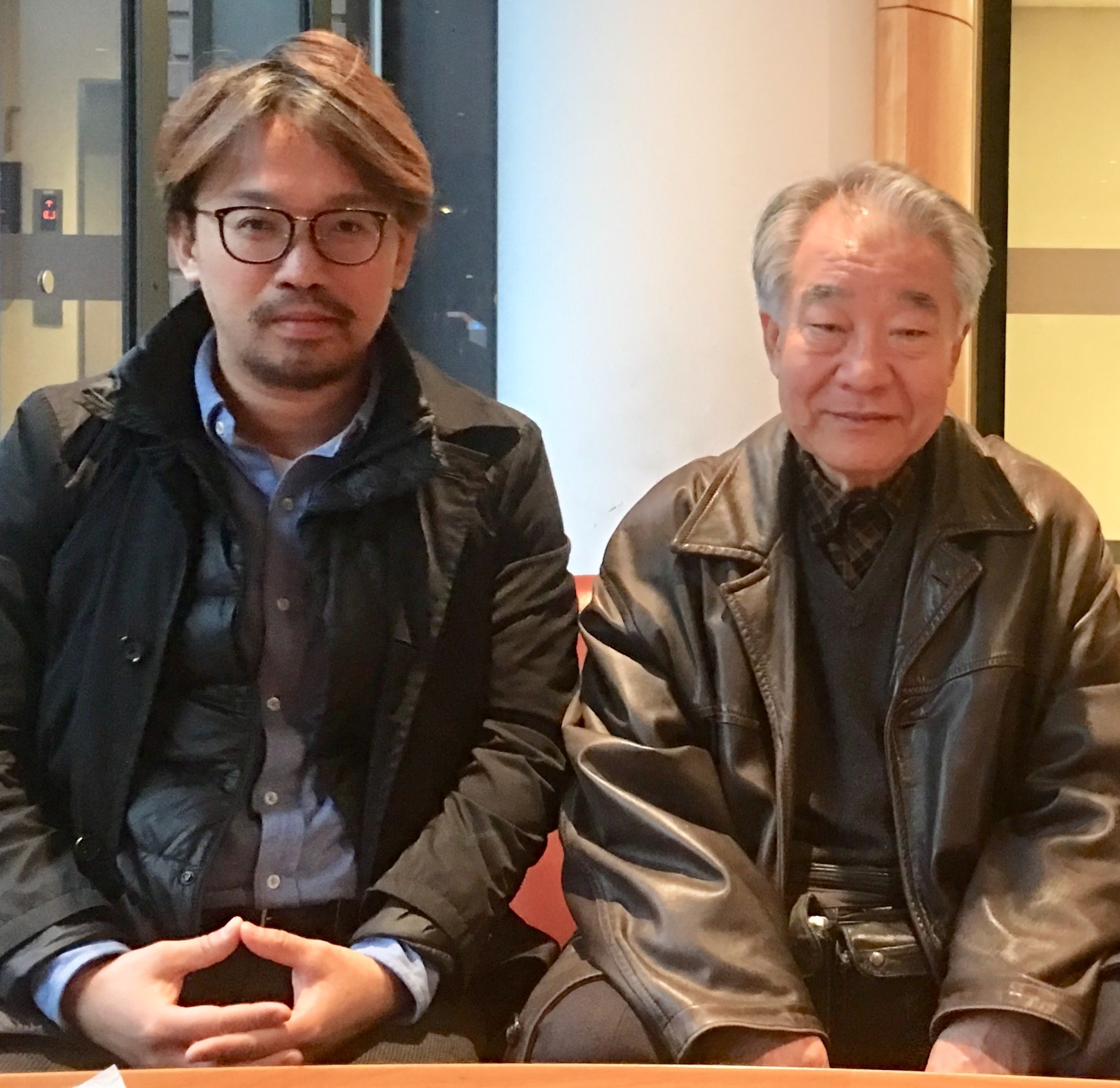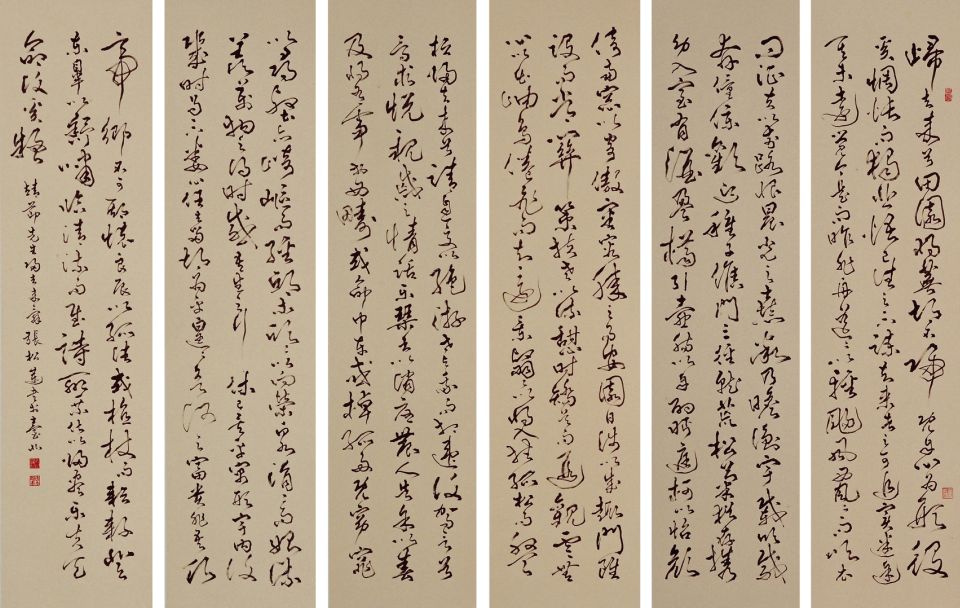傑克‧康菲爾德(Jack Kornfield)在其著作《狂喜之後》(AFTER THE ECSTASY﹐THE LAUNDRY)一書中提到靈修團體所面臨到的四大困境領域,開宗明義即指出靈修團體最常見的危險在於權力的濫用,他認為這種情形最常發生於既定團體身上,身為老師或大師的人攬控了所有的權力;其次,第二個最容易滋生的問題是帳目不清,他舉出了信眾進入靈修團體之後,心中對上師極其感恩,往往所捐獻的金錢會如潮水般湧入,乃至,最糟糕的是,特別對於那些在靈修團體上,某些權高位重者之士,私底下卻過著不為人知的奢華生活,「一方面無恥揮霍同修的捐獻,一方面還要求其他的團體成員過著嚴謹清貧的生活,或是投入義務工作。」第三點,他提到了「以宗教之名進行性侵害」。有些學生往往為了接近老師,而以「性」來作為手段,以換取親近老師的機會,或是藉由「坦特羅」(Trantra)的修練之名而向上師獻身,或其他形式的性剝奪。最後,最常見的問題是酗酒與濫用毒品,這些問題,雖然早有耳聞,不過,藉由此次的機會,期盼同時間的反思在靈修乃至於禪修活動之中,在團體運作中所面對之困境,當然,絕大多數的禪修者無非希望能夠體證出生命之真諦。
雖然這本書的內容,對於佛法上所謂的「涅槃」之法義有誤解之處,但是,卻對於當今靈修團體上所發生之問題,一一揭示出來,也確實對於想要參與靈修者,或者已經參與其中者,作為一面值得深思之借鏡。人為什麼會參與靈修(或者是禪修)之後,還會對於「權力」有那麼多的執著性?參與靈修者並非皆是以同樣的理念或者想法加入了「欲出離或者是欲證悟」之團體,「私心自用」的人也存在並且依附於團體上,經歷過對於「權力把持」、「權力控制」而品嚐了權力的滋味,又利用了人類喜愛「崇拜偶像」,以及心靈空虛者對於世間上所謂的「靈性大師」等物化表象之心態後,發生了問題卻又往往不自覺,某些做為學生的也許還非常贊同此種縱攬靈修團體權力之「中央集權」大師之所有作為,他們會認為,只要是老師所宣說、流傳的教誨或者是顯露出的行為,無非皆是「良善的」、無非是要讓學生「反省的」,完全不加思維「老師亦會犯錯」之機會;對於居上位者、掌控團體權力者(其實,嚴肅的來說,佛教並不認同在靈修團體中,老師能夠擁有多大的權力來控制學生的思想與行為,以佛陀本身之切身經驗來說,他也提到「佛在僧數」之類的話語,而摒除了對佛陀產生依戀、崇拜之心理狀態,他提醒學生千萬不要崇拜老師,當老師者,亦勿自以為是的認為自身證量比學生高,而心懷貢高我慢)會有這種「權力把持」之作為,我想,不僅是參與當中者所應面對之事實外,乃至於離開了此類團體之學生亦需要負起這些讓整過靈修團體完全走樣的責任,能夠直言不諱的學生,才足以讓自身所參與之靈修團體,有正面增上之效用,反之,只能讓團體跟著老師之權力欲而漸離「證果、出離心」越行越遠罷了。
再者,金錢的誘惑,與權力的誘惑有等值之效用,對於那些亟欲布施靈修團體者,往往一股腦兒就把大量的金錢捐獻給自己所參與或者所認同之道場裡,而對於靈修團體之整體金錢用途,也不加以過問,凡是認為只要是團體所做出之決策乃至於老師所出支之費用,不論是用在哪裡,皆同上面所述的一般,皆是「良善的」,一個靈修團體如果帳目不清,乃至於要與會者大力布施的話,我以為也許在更長久的未來之中,必定會發生「老師佔用公款、有權力者私心自用」之機會發生,如果一個靈修團體,發生了帳目支出之名目交代不清的窘況,乃至於產生團體中的帳目往來於掌權者之口袋中,如此之作為,當無可能於修行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絕大部分的宗教強調「簡樸生活」,如果作為學生者無法質疑、也不能質疑老師之作為,我想,這絕對無法讓自己的「靈修」有所成長,同樣的,歷史上一再的證明,越是封閉的、不接受建言的團體,越是避諱於挑戰、質疑老師的權力與作為之團體,必定不能給予學生們真實之修行,有的話,亦只是自欺欺人爾,因為關心團體的運作,才會在團體出現漏洞時,直言團體所正在發生的缺失,藉以彌補並且解決這些問題之存在,靈修團體也是需要「批判者的存在」,更正確的說法是,要有作為一位靈修者所當有的良知與直言的勇氣才是。
在我所遭遇過的靈修團體之中,我想,絕大多數皆是嚮往真理的,也不失其所謂「靈修團體」之名號,但,「人類的問題總是淵源於人類自身的貪婪」,我聽聞有些團體藉由「靈修」之名義,來對學生倡導「男女性愛」之說,再藉由種種的詭辯之術以及運用人性最空虛、最脆弱之一面,讓那些單純的求法者,認為上師確有幾分證量可言,而極崇拜這些以「神通」、「消業障」為口號的上師,再而真信可不伏除對於男、女欲愛之貪求而證果之事,當學生無法克制性慾時,則又以「業障來臨」、「著魔」之說來恐嚇學生,或與其他與會者共同對此學生施以「棒打之術」來對治她的「業障」,這些問題的發生,自古以來,總是不斷的發生,尤其是蠱毒巫術盛行的時代,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那些自詡為「高知識份子」身上,更是對此信受不疑,為什麼當今在靈修團體中,所面臨這些問題的,總是不乏此類「高知識份子」?除了對於修行之認知出了問題而誤信修行乃為「神秘之術」外,還有就是此類高知識份子只講求於專業知識上之訓練,卻忘了對心靈「反思」、「質疑」之重要性;信受於眼前自己所認知的表象世界,卻忘了著手對「聖教量」之確實瞭解,反倒是對於「人」的信受不疑取代了對「經典中的聖教量」的認識;「我很感恩老師,所以我要布施我的色身給老師享用」、「老師的所作所為絕不會出錯」、「老師所證悟、體悟的境界一定比我還高」等先入為主之臆測,早已出現眾生看似寧靜的海平面之下;別忘了,「證果的與否」不在於自己是否對於「知識擷取的多寡」,而在於自身是否能夠契合、證入經典所闡述的領域。凡是老師所以為真理者,做為學生的亦應當仔細思維才是,我並非是個「懷疑論者」,因為就佛教的教義來說,秉持著「懷疑論者」的論點本身就是錯謬的,因為這類立論者,是否連他所懷疑他人、所不信受他人論點的自己本體上來說,亦需要懷疑?懷疑了自己所推算出來的懷疑,卻又以為這麼做又是符合自己的言論,那麼,「符合」本身是否即表詮於「懷疑論者」本身之思想?其實,一位欲修行、正修行者,當是個「質疑論者」才是,甚至應當說是【凡是有違於「聖教量」者,務必要去質疑問題背後所影射出來的知覺事件,此類之知覺事件必是虛幻的現象】,「聖教量」之所以能夠接受後人不斷的考驗與思維,自有他存在於世間上的道理。
總體上而言,人為了經歷「神聖境界」之感受性,往往可以付出許多代價,但應當思考所付出的代價,是否確實契入你所信受的宗教經驗以及所宣揚的教義真實性,若違背於一般經典所舉示的「持守戒律、澹泊名利、清心寡欲」的作為,反而喜愛使用一些「特殊事件與機率」來詮釋自身因為無法嚴守戒律的浮亂末那識所現行的我愛,無非是不斷的讓自身一再地離開「靈修、禪修」越來越遠,也更讓自身的修行經驗越來越退步而已,真正的靈修經驗應當是境界現行的越來越少,而自身的種種貪、嗔、癡三毒業已降伏才是,歷緣對境的煩惱尚且不能降伏,更何況是無相之法性海?在佛法上有個許多人熟習的經文,它是這麼說的:「末法諸眾生,口但喜言空,實際卻行有。」越是追求境界者,越是執著於境界,「雖然他們總是說自己已經證得無相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