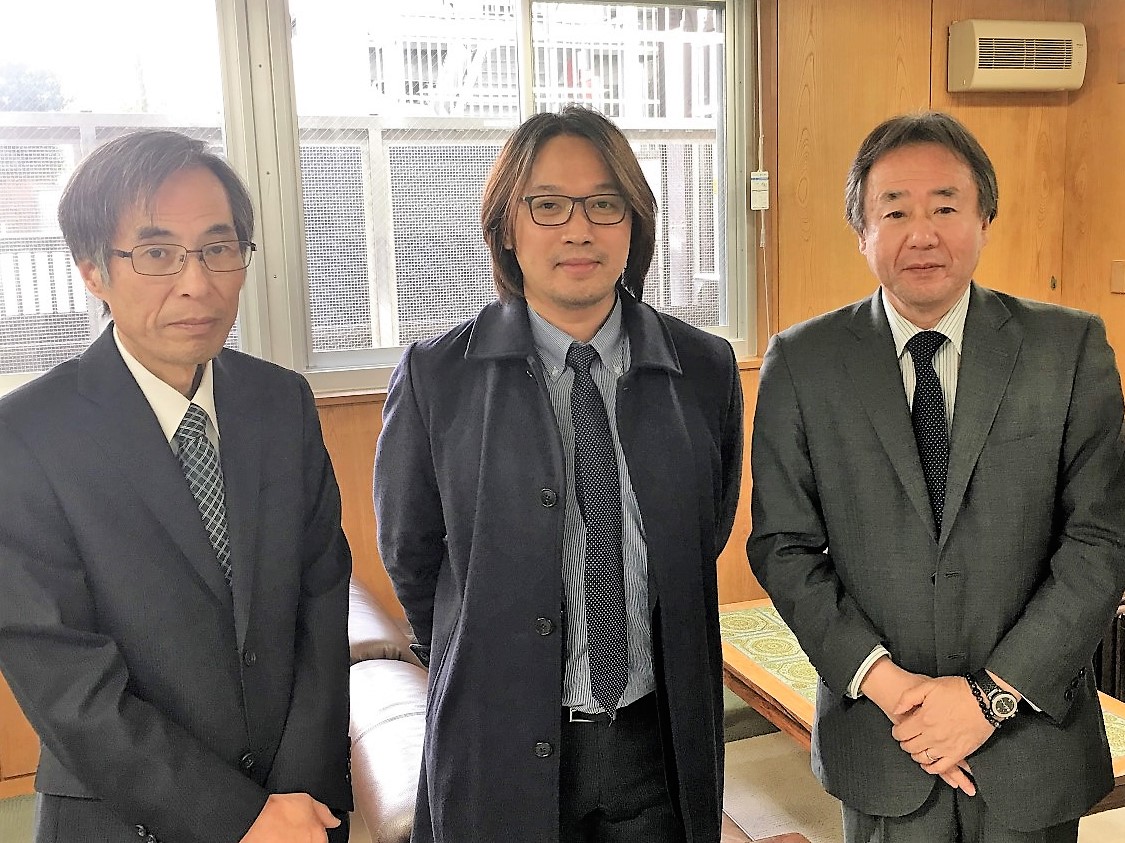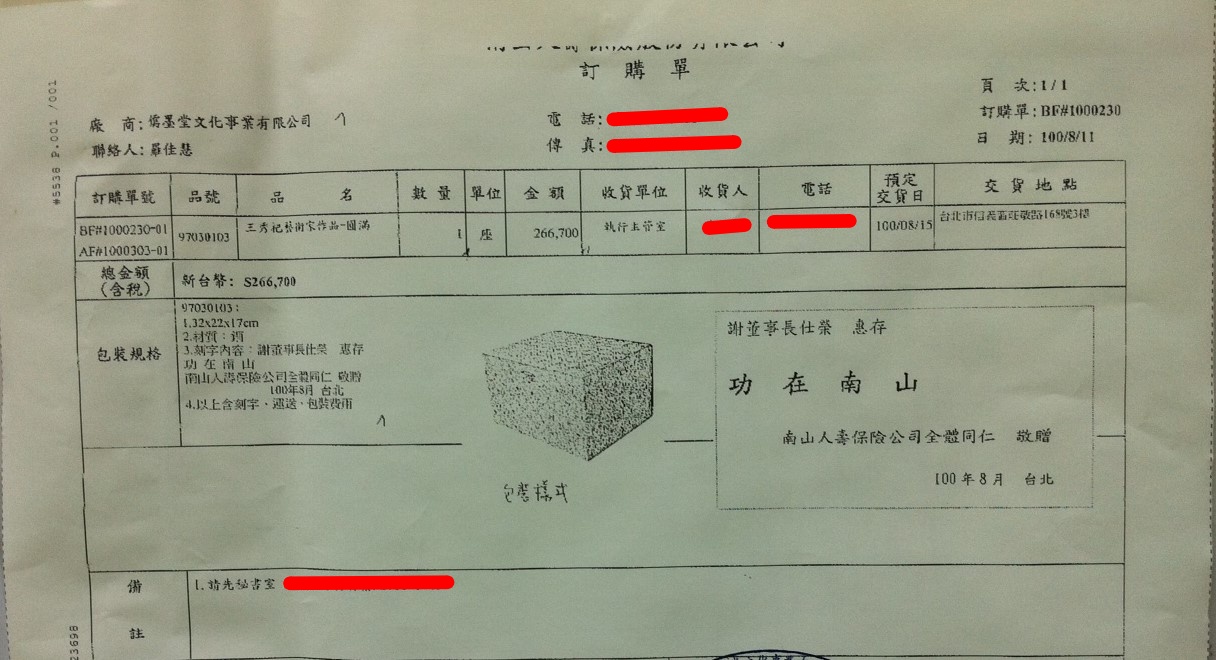《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首次出版之著作時,梁漱溟先生才二十八歲 ,影響了許多當代中國之新思潮,雖然粱氏後來棄「佛」入「儒」(他認為佛教業已不適合當代有情之深層改革。),不過,對於一位學習佛法的人而言,他的著作還是需要作一番深入之研習的,以其善法之觀點而言,亦無不可。
他在第五章之《世界未來之文化與我們今日應持之態度》裡,其中的一節《今日應再創講學之風》,有一段話是這麼說的:「至於我心目中所謂講學,自也有好多與從前不同處;最好不要成為少數人的高深學業,應當多致力於普及而不力求提高。」學業之薰習並未成為根本上之問題,然問題者,端在人心之造作。我對這段話,頗有感受,雖然並不完全支持這樣的思想模式,但,對於現今學人而言,修學佛法者,是否只能獨善其身,而不能兼善天下?而忘了菩薩大悲願?
佛法之修證應當能夠契入有情之根器而為,如喜聲聞乘者,自當與聲聞乘之教法;如喜菩薩乘者,自當給予其菩薩乘之法理修持;如喜佛乘者,自當勸勉其深修唯一佛乘;然絕對不可混同於外道氣功之學併同佛法之修持,如此混同不分,必有弊病。現今修學法相唯識學者,實為少數,問題不在於三轉法輪之唯識學上,當如前面所說的,全在於其「根器、種性」之不同,而有不同之薰習。有學人以為,「唯一佛乘」實在是比修學「法相唯識學」更為殊勝,然卻又不知其「唯一佛乘」之所以然,「唯一佛乘」是需要遍學諸法的,過於排斥教理內蘊之深義,亦必定不可能為「唯一佛乘」之種性者。
隨便藉此拈提,有時候,真的只能隨其因緣而不可強求,那麼,人世間一切的事物不也是同樣的道理嗎?懺悔、懺悔。
窗外還有那麼靜謐的雨聲陪伴著他,獨自喝口茶。過度的貪求同樣的也造成了心靈之萎縮,重複的動作、重複的思維,真的是該休息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