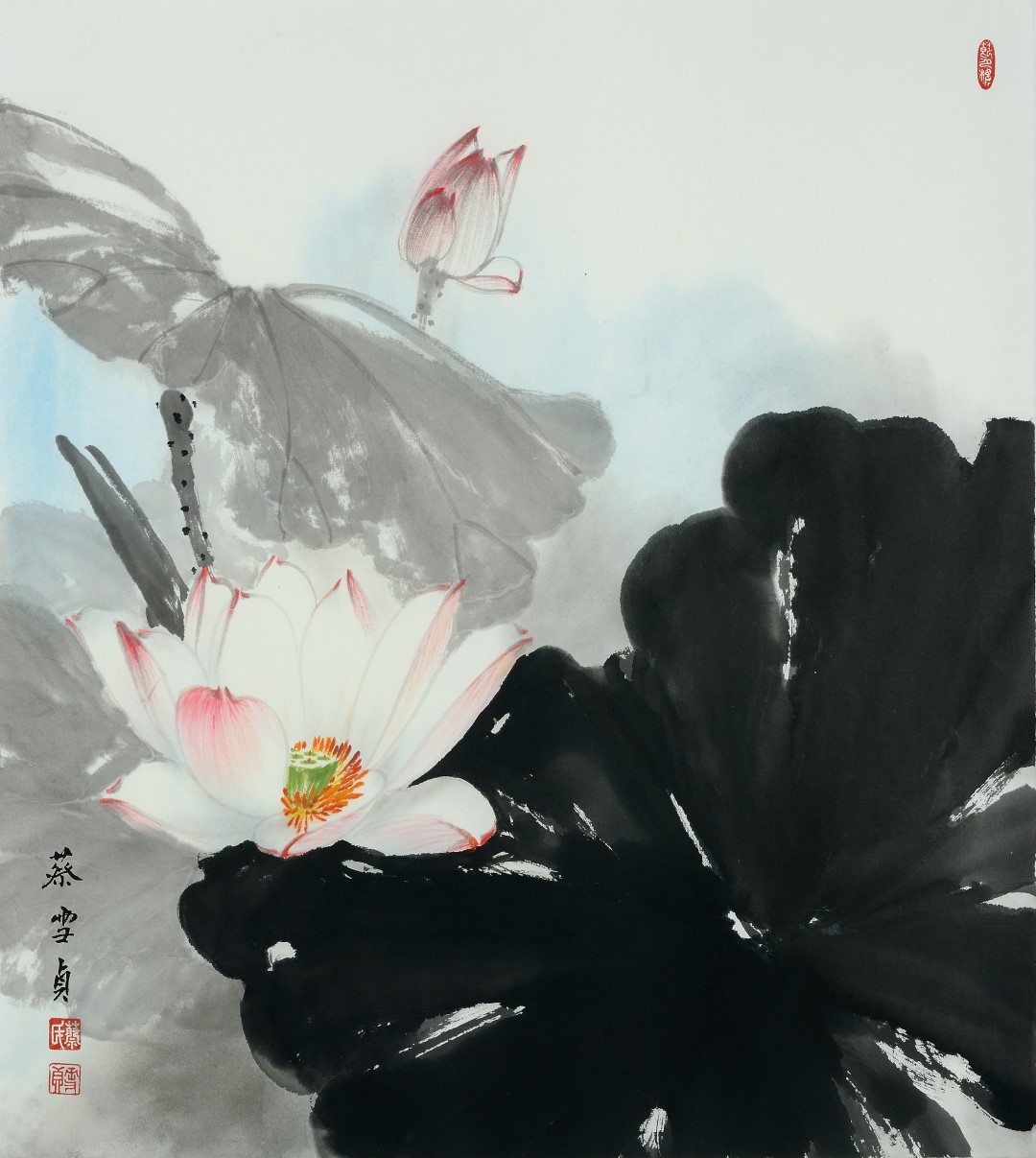奈良的東大寺,於春、夏、秋、冬四季之際時常參訪,參訪完畢,會於奈良公園附近之湖畔內靜坐些許,寧靜的時刻,依然記得。東大寺為日本華嚴宗祖庭,為日本聖武天皇所建造,該寺供奉盧舍那大佛與洛陽龍門石窟所奉大佛相同,雖佛像建構不同,然皆為盧舍那大佛,該寺盧舍那大佛後由印度菩提僊那法師開光,聖武天皇日後出家為僧,為東大寺四聖:菩提僊那、聖武天皇、行基、良辨。行基重視法相唯識,而良辨雖為華嚴宗二祖,然也精通法相唯識學。奈良時期又為南都六宗所謂華嚴宗、法相宗、律宗、三論宗、成實宗、俱舍宗之弘揚地,而此時所謂之宗並非為宗派之意,僅只是作為僧人研學不同而分學派,與現今之宗派義不大相同。
「儘管遇到許多阻礙,卻沒有讓聖武天皇放棄建造盧舍那大佛的想法。工程在天平十七年的八月時,先整建了用來講說《華嚴經》的道場金鐘寺,並重啟大和國的金光明寺——也就是日後的東大寺。此後工程順利進行,到了天平二十一年(七四九年)時,大佛整體已大致完成。而在此時,陸奧地區發現黃金的消息和樣品也送到了宮中。
當時許多人相信日本並不生產黃金,因此連天皇也苦於該如何確保鍍金用的黃金不虞匱乏。當發現金礦的消息一出,聖武天皇感到無比的喜悅,過去困擾心頭的擔憂全化作了感謝。該年四月一日,天皇行幸東大寺,並在尚未完成的盧舍那大佛像前,命人北面而立,宣讀以「三寶之奴天皇」開篇的敕文。這篇文章裡寫道,天皇對天地自然終於回應了自己的想法。
在祥瑞災異思想之下,天皇把產出黃金這件事理解為「大瑞」,並說到「朕豈能以一人獨享此大瑞,應與天下共頂受賜,歡理可在」。天皇想將喜悅分享出去,於是開始一連串對官員們的加官晉爵、大赦身陷囹圄之人,並賞賜發現了黃金的人們。此外還將年號改為「天平感寶」(《續日本紀》六十五〜七十九)。
到了該年閏五月二十日時,天皇下詔「以華嚴經為本,一切大乘小乘,經律論抄疏章等,必為轉讀講說,悉令盡竟」。並向東大寺等十二大寺提供粗綢、棉、墾田地等(《續日本紀》八十三)。過去,天皇並沒有具體提及該經的名字,這是首次將《華嚴經》向社會公開。不僅如此,聖武天皇還宣布將《華嚴經》作為根本經典,表示出他對該經的義理應該有相當的理解。這裡要特別注意的地方是,聖武天皇並沒有意圖排斥《華嚴經》以外的其他佛典,反而勸誡僧侶,要對一切經書和論書進行「悉令盡竟」的研究。」---《人類該往何處去》
問:何為戒殺?
利根者,聞說行者「應當戒殺」四字,即能自行觀行任何形式的殺皆是殺而止殺,於字字間薰種現行而能戒止一切殺心、殺行。
鈍根者,聞說任何形式的殺,不能止殺,須聽聞多說戒殺之理而後於境界現行ㄧ一觀行而止殺,於此止殺之行雖然遏止,然於止殺之心無能遏止。
愚癡者,聞說戒殺而說他殺我亦殺,無能遮止一切殺,縱令聞說亦不思維觀行隨無明所飄而讚嘆殺、默許殺、隨意而殺。
測師於《解深密經疏》引《善戒經》說:「菩薩戒者,非口所得,心口和合,然後乃獲。」心、口不能和合,則不能得菩薩戒,縱使受戒亦不得,無菩薩種性故。何以故?口說戒殺,心行殺意,即非菩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