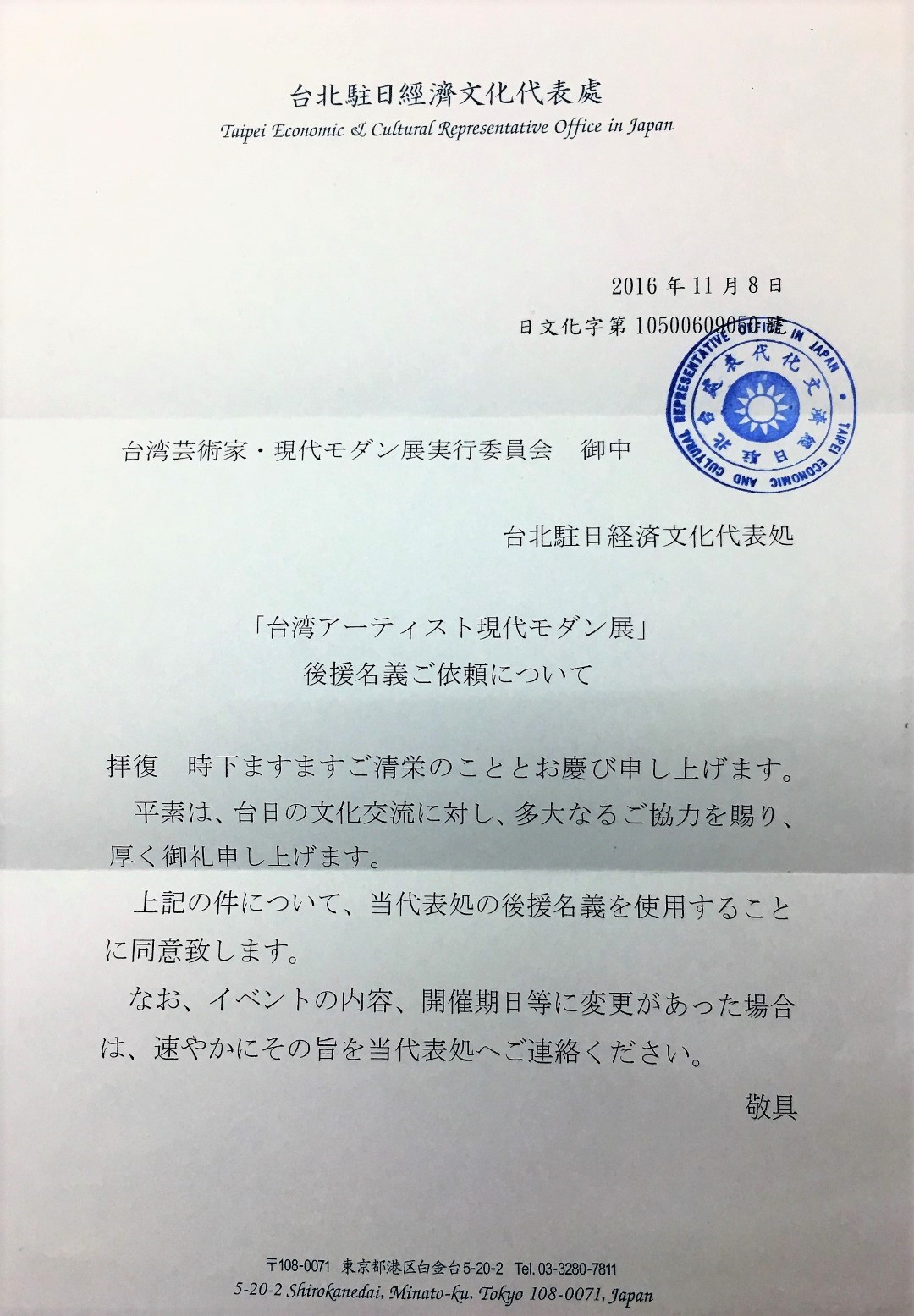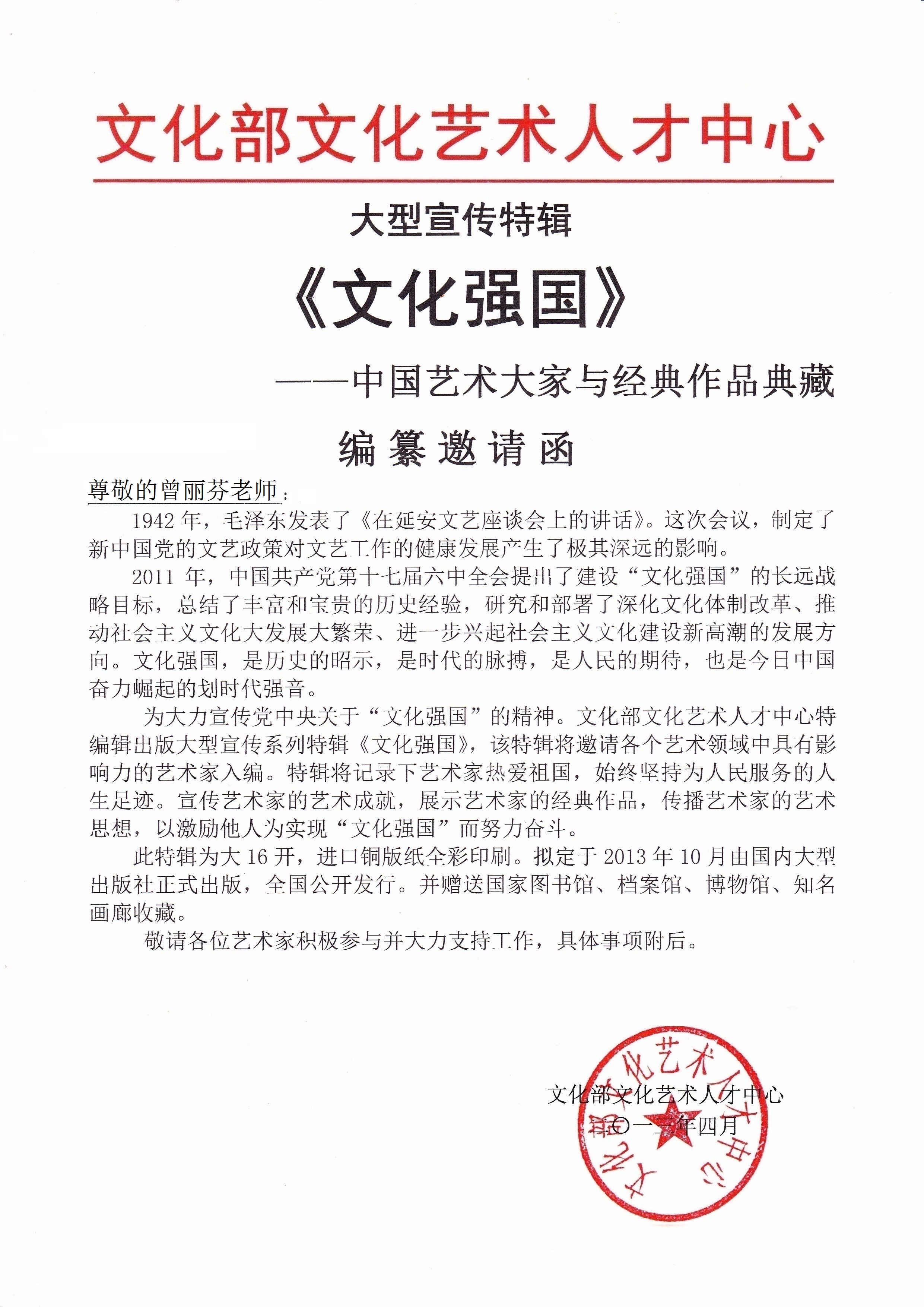前言
此文乃與某法師於虎年對談所成,該師於俗時,業以勇猛精進,出家為僧後,更是如此。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故後又稍加整理。
不輕菩薩於世俗勝義皆說法無畏,盼望學人亦應當效法不輕菩薩。 傳者,傳揚、傳導、傳佈,然我等尚且未證果,如何傳揚、傳導、傳佈佛法?應當用漢「語」佛教為佳,謙遜義故,以語表義,又能突破世俗地域限制,如今基督宗教尚且有漢語基督教等研究,佛教者,亦能超越彼等。古德諸師不論身處中亞或者他處,若無文字記錄則難以追蹤,若有諸多領眾等,亦能薰修。因世俗制度封鎖,是故難以如印度托缽等,也是沒辦法中之辦法。
談念佛與熏習
增上心、慧二學由增上戒學而入,不輕菩薩與彼二菩薩所行看似不同,然實際上皆菩薩萬行,本生等事不並侷限於同樣之作為,本人對此不擅長計算某菩薩行多少事、某菩薩又有多少差異功德。報師恩並不僅只限於自宗,或者現今存在之師,乃至無量無數於菩提道上前行之諸師,隨時憶想即能不被名利所誘,彼等諸師於諸逆境如王難、法難等,尚且不愛於此色身能捨命以求佛法,何況我等愚癡凡夫?如基師言:「現量照自體故,是五識等四分之中自相分故,識所變故,今說為有,亦能變識;後時意識所執外為實色等境,妄計情有故,說彼為非有。此明內心變似色等現是心之相分,此但非外,妄計所執心外之法是無,說彼非有,不稱境故。」唯識所言即在於此,不離識變,以此遣對色境執取。
如念佛成片,亦為名言薰習,如奘師所彙《成唯識論》釋《中邊》言:「應知諸法有空不空,由此慈尊說前二頌。若諸色處亦識為體,何緣乃似色相顯現?一類堅住相續而轉,名言熏習勢力起故,與染淨法為依處故。謂此若無應無顛倒,便無雜染亦無淨法,是故諸識亦似色現。」此中所言即與大論相類,諸論能會通。
若無熏習勢力,則無能念佛成片,而成片時,於色境上無一不現起念佛之相續念。色境若為實有,於修止觀中則無能轉種種色境,雖觀極微乃斷身見。修止觀修念佛最得當,削伏自身習氣最得力,如念與自身有因緣之佛菩薩,隨時保持憶念,即能逐漸於此中理解色境絕對非實有,世俗人何故對色境執取為實有,乃因不解為識變自相分非餘,識既能變亦非於勝義實有,此中離能所等,於後即與 龍樹菩薩所言相同義。諸多學人學瑜伽、唯識等義,皆未明白變義,進而執取藏識等為真實有法,實際上,密嚴所言乃自受用土,不過從有情自身之大幻獸轉依無漏身土爾,畢竟有「變」義。念佛憶想只要功夫到了,自然能解。如諸俗人整日憶想世俗欲愛等事,亦不需他人教授卻又能日日夜夜思維、憶想此等欲愛名利等事,只不過念佛憶想乃緣於佛諸功德等事,又如緣 彌勒菩薩等事,本出於《觀佛三昧海》,此經翻譯者為尼泊爾人 佛陀跋陀羅三藏法師,法師於當時常被 什公論議佛法等事,顯見 佛陀跋陀羅三藏法師於三藏中解諸法義可能勝於 什公。
談環境與習氣
人生苦短,深覺自身於環境所影響諸多有漏染法之熏習於自身多為無意義,不若直心面對一切人事,順逆皆無所畏懼,畢竟一切世俗權、名、利等皆為是苦,於此等苦又做種種愛著等想、行,則又是愚癡了。能出家,已經甚好難得,又能於現今諸多限制之環境發菩提心出家,更甚難得,出家一日勝於在家一世。
其實可能是整體環境或者可以說數千年來整個華人社會所導致,生活於中往往不能夠直心語言,顧及過多也或者因制度不同而思維不同,傳統有好的、但也有其缺陷,如儒家與儒術各有不同,一為修身等義、一則為古君王令國民呈服並崇拜其為上帝等制度,而生活於其中,也往往難以轉離社會中所建立之共業,現行了則又往往被影響,又於種子熏染。台灣雖然轉型民主制度業已數十年,然雖移民數百年,亦帶有華人習氣,特別是言行不一等染習,此於日本等國生活即能知曉習氣現行之種種差異。
現今諸人喜諂媚之語、非如實語卻又稱為「善語」,實際上非也。諂者, 彌勒菩薩解:「心不正直,不明不顯,解行邪曲;故名為諂。」 無著菩薩《顯揚》云:「諂者:謂為欺彼故,詐現恭順,心曲為體。能障愛敬為業。乃至增長諂為業。如經說:忿、恨、覆、惱、嫉、慳、誑、諂。」善語者,悅意、無染、唯善所攝。世俗人習氣善良者多半亦如實語,如得一分錢即說得一分錢、失一分錢即說失一分錢,不必聖者即能如是。彼等雖未深入佛法,然諸多善行亦需思維彼等何故較我為勝?並於彼等所行、所言而生慚愧心。
談增上心學
身分支節血肉能還原如初,除佛力攝受之外,一般大抵還需要有四禪之增上心學加修通明禪,如天台 智顗大師《法界次第初門》:「言通明者,辨此禪相具出《大集經》中,但經不別出名目,而北國諸禪師坐證此法者,欲以教人,必須標名傳世。若用根本禪說,雖定名一往相似,而行相迥異,還用此名說者,行人便作常解,則大乖其妙。若安十六特勝觀法,雖小相似,而名目都不相關。若對背捨、勝處等,名之與觀,條然併異,既進退並不同餘禪,豈可用餘禪名說?故別為立自名,名曰通明。所言通明者,修此禪時,必須三事通觀,故云通明。亦以能發六通、三明,故云通明。」此中即說修通明發六通、三明。於當時北國諸禪師之說,若按隋朝解,可能為東突厥、契丹等國,然亦有可能指陳的為「北魏」,北魏拓跋氏多為鮮卑族,如曇鸞即為北魏時代,曇姓多為康居人移民,與華嚴宗法藏師相同。如《續高僧傳》言:「北國虜僧曇鸞故來奉謁」,當時北魏算是中華文明燦爛之始。慈恩基師俗姓尉遲,先祖亦可能源於中亞于闐,是故先前所言《成唯識論述記》古本於新疆被發掘,極有可能亦與當時北魏、隋、唐之際多為鮮卑、突厥文化影響整個東亞文化圈,而諸多僧俗多半於當時亦為鮮卑等族,於當時學漢語乃北魏拓跋氏為了爭奪「中華」正統所致,故彼等鮮卑族人自小多習四書五經之漢語。
天台除四教,若按《摩訶止觀》解:「通明禪發相者。上特勝修時,觀慧猶總見三十六物,證相亦總。通明修時細妙,證時分明。《華嚴》亦有此名。《大集》辨寶炬陀羅尼,正是此禪也。《請觀音》亦是此意。修時三事通修,能發三明六通。又修寶炬時,乃至入滅受想定,當知此門具八解脫、三明、六通,故名通明也。」於後「修寶炬時,乃至入滅受想定」當為聖者之流,又按《妙法蓮華經玄義》解:「又進宅內名「入」,入見群臣豪族,大功德力,聞寶炬陀羅尼,見不思議解脫神變,故名「入」也。出者止宿草庵,二乘境界名「出」也。心相體信者,得羅漢已,聞罵不瞋,內心慚愧,不敢以聲聞支佛法化人,心漸淳熟,如從酪出生蘇,是名從修多羅出方等經,即第三時教也。」 與此能會通,當為證阿羅漢果位。若僅只講神通,則需修四禪方能修通明禪。
其實,不論四阿含(或五阿含),到大乘佛教諸經,如《般若》、《法華》、《寶積》、《大集》、《涅槃》、《經集部》等,皆有提及關於色身觀等修學,加諸其他語系之相關論疏,若日後整理亦是不錯,畢竟論疏所言過細,一般學人也難以能發願深入其中,而《修行道地》等經,其實也算是瑜伽之一。若能按不同語系整理而書,互相比對與深入,對於增上心學等亦能俱眼。
解義
無忘失法,於《攝論釋》如是言:「由轉識蘊依故,得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此中大圓鏡智者,謂無忘失法,所知境界雖不現前,亦能記了,如善習誦書論光明。」又他本云:「由轉阿賴耶識等八事識蘊,得大圓鏡智等四種妙智,如數次第,或隨所應。當知此中,轉阿賴耶識故,得大圓鏡智。雖所識境不現在前,而能不忘,不限時處,於一切境常不愚迷,無分別行能起受用佛智影像。」若按《攝論》後解法身者,則知法身為一切四智功德所依。恆住捨性與無忘失法義同,圓鏡智依清淨法身故。
頓現一現者,通《瑜伽》:「復次,於色聚中曾無極微生,若從自種生時,唯聚集生,或細或中或大。又非極微集成色聚,但由覺慧分析諸色極量邊際,分別假立,以為極微。又色聚亦有方分,極微亦有方分,然色聚有分,非極微。何以故?由極微即是分,此是聚色所有,非極微復有餘極微,是故極微非有分。」又基師《雜集論述記》:「《華嚴經》說菩薩能知無色界宮殿若干微塵成,五十四云『略說極微有十五種』,如是等教,處處非一。極微無者,彼如何通?雖無真實極微體性,如慧所析,彼量亦成,說知彼極微如所析量故,五十四說非集極微成麤色故。《成唯識》說:『然識變時,隨量大小,頓現一相,非別變作眾多極微,合成一物。』《瑜伽》亦說:『由諸聚色最初生時,全分而生,最後滅時,不至極微,中間滅盡,猶如水滴。』此言意顯,如熱釜,水煎漸滅時,不至邊際,諸色頓盡。」
密教所言者,大抵不離色相觀,是故多半取相修觀。此等東密傳承亦有此說。其實不只日本天理大學等收藏漢語佛教諸多古本,如日本橫濱《金澤文庫》亦多有密教等論疏、傳法灌頂等藏,最近正在展示傳法灌頂諸文物,先前住於日本東京、橫濱等城市,《金澤文庫》離市區較遠,靠近橫須賀。總之,若未來有時間,若能於日本尋寶,即當知曉諸多漢語傳承之所不斷,如八宗、十三宗等義,實際上乃是日本佛教所建立,於古之中國當時並未有真正的建立者,古德也許多不願自立門戶。日本目前已經有數百個宗派。華嚴宗等短疏,李通玄居士等著作亦應當閱讀。
《梵網經》日本諸師註解,可再參酌如日本真言宗 諦忍妙龍法師《梵網經要解》即融入六大、四曼、兩部等義。而法師另外一本著作《梵網經要解問答》則多用問答解釋,亦多加入表解等形式。 諦忍妙龍法師於十五歲即修四度加行,除了本身為真言宗外,亦傳佈律宗、淨土宗。師曾住持之興正寺,位於日本名古屋,現今亦存在於該市,靠近名古屋昭和區之中京大學、名城大學。
如有說「此『非自性有』即『非自然有』,乃『如來藏』真如不生滅性,然卻隨煩惱造業之緣而顯現如幻之自性相。如《解深密經》云:『由於依他起執著遍計所執自性,起諸煩惱,由彼作業流轉生死。』」即不生滅性又如何隨煩惱顯現如幻之自性相?既有不生滅性焉如何又有生滅性?後又引《深密》解依他證真如不生滅性,按此解,亦訛也。此解即等藏識同於真如不生滅性。
《瓔珞經》於日本東密或三論宗文獻亦有。雖為沙彌亦不可輕,如於僧之前即勇猛精進,如何能小覷?又有諸師於自身所撰內容紙本數位本或者網站等數位平台將古德放置於後、自身置前,於師於俗亦有不尊敬義,如世俗父母列隊於子女後、又或父母老邁卻自身前往子女家宅過日,子女雖迎父母入堂,然未恭敬,又與人談時,未令父母先行,皆屬不尊孝養長輩之舉,更何況於出世間上上學之佛法?縱然論據不同,亦應當尊敬,更何況所依為其宗?
後學思維先前書信往來將「阿彌陀佛」置於法師稱謂之後,此為不正之事,不論紙本或數位書信往來皆應當置佛號於法、僧之前,於此悔過說明。又現今學人註解經論以後論替前經,如《某論》註解《某經》,書名當為《某經某論釋》,今之為《某論某經釋》,以後之論置於佛說經於前,著實大不敬,不論諸經或諸宗爭議如何,皆不當如此。如同世俗長幼有序,何況佛弟子等僧俗?又如翻 龍樹菩薩《大智度論》,本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釋論》,即知以經為首、釋論為後,敬佛德故。
談色身無常
後學幼時早產亦常患病,出生之前,父母於本家台南麻豆經營皮毛工廠,麻豆又為西拉雅族等共居之處,又為台灣豪族之所,大抵不是出知識分子、官員就是出企業家。當時專門養兔子每日請工人剝皮用以外銷,然出生之後,因日常生病,母親又開始學佛,始知此等事業乃是殺生,了知戒殺方為根本,就收掉當時頗具規模之工廠,愚之色身日漸正常,此即殺業所感之共業。爾後稍長始練武術、健身等,後又十餘歲開始學靜坐等,色身就自然逐漸健壯。此等亦可能於共業之中,色身感發之後,讓有緣之父母了知一切殺業皆不可行而現行,爾後父親常見到有諸多野生動物被農人所抓,父親就時常放生此類野生動物。
台灣民間俗語:「久病成良醫。」確實,色身過於健康則難以生起無常想、亦難以想要深入佛法,除非人生遇見大因緣才可能自覺而深入佛法等事。母親也正是因為後學幼時色身多諸病苦而到處尋覓民間信仰,最後歸依佛教,或許正也是每位有情之因緣。台南麻豆為近代台灣最早接近歐美文明之地,約莫四百年以前就有西方傳教士於此傳教並且編輯諸多語言學辭典,每位有情誕生不同地方都為過、現之異熟果報所在,顯見異熟果報之不可思議,如同古之洛陽多出高僧、或世俗文豪等,建造高樓大廈僅需幾年功夫,而累積文化需要數百、上千年,而要毀壞文化只需一彈指即可,此即共業所感所導致。
所舉《入行論 忍辱品》為33、34頌。佛陀跋陀羅三藏所翻《佛說觀佛三昧海經》,若按《一切經音義》解「烏瑟膩沙」(梵語也,如來頂相之號也,《觀佛三昧海經》云:「如來頂上肉髻團圓,當中涌起高顯端嚴,猶如天葢。又一譯云:無見頂相,各有深義也。」)。此中可再參酌真言宗小野流 覺禪師所著百餘卷《覺禪鈔》〈佛頂部〉,該宗派為日僧 仁海師所創,與孟加拉僧尊者 阿底峽,同為十世紀人,顯見佛教按語系分布之不同,藏語佛教於十世紀後深受孟加拉、印尼佛教影響甚深。而 佛陀跋陀羅三藏影響了漢語佛教修止觀等傳承,現今諸多學人大抵忘卻了。增上心學攝陀羅尼等,於《瑜伽師地論》亦能看出與《大智度論》意旨相同,而「明」義,本就需以增上心學為基礎。《往生論注講義》同名另外亦有早期性梵長老(1920-1997)曾經著作過。其實一切宗皆會歸於相、土自在之淨土,不論是中觀、唯識乃至密教。
談共修
禮儀與修養或者對自身文化的認識,對於學佛非常有助益,特別是現今浮躁社會來說,因為知識取得容易,但也往往不珍惜,又或媒體所播多半講究仇恨對立,導致自身更容易受影響,是故靜謐的觀察身、受、心、法於隨時,不論日常生活或於睡、夢之中,都能細細觀察所浮現種種影像而生對治,著實重要。
僧團之目的常常能夠互相勉勵共學,並按次第循序所說所行,佛寺本為佛學院,古之佛寺本為教育僧俗共修用途,這點是正確的,倘若日後若再能參酌漢語佛教日本傳承教授,應當會更完整,畢竟日本從三世紀由百濟傳承至今未曾斷絕(雖法相宗、三論宗等已經式微或併入真言宗等宗派),而古之中國曾經歷三武二宗滅佛運動,加之距今不過五十餘年之文革浩劫,或多或少亦僅存少爾,如今本為中原佛教發達之地,已經逐漸凋零,又或甚少能深入經藏者,縱使有之,亦多半帶著名利心、爭鬥心以發達於世俗。所幸現今網路世界發達,渠道亦廣,於承先啟後亦能讓學人深入三藏保持傳承。現今佛教團體另外設置佛學院,可能是有些佛寺僧才人數少、或者已經缺少師資、又或自身未能深入諸語三藏而需另外令僧眾往佛學院就學。
僧團修學共修期間自然需集體修學,難以有自身時間,若能逐漸深入增上戒學等,亦是出家目的之一,必乃善事。台灣現今多有出家法師多年後離開僧團獨自或三五僧人聚集共住他處,所以時常能見到馬路上或者捷運等處多有學僧背著後背包到處參學,不論團體大還是團體小乃至個人(雖然按出家律來說一人不能稱僧團),只要深知我們今生修學佛法之目的、動機與意義,不論在哪,時時刻刻提醒自身,則不會被大環境所影響,若環境影響甚深,我們則於此觀無常、苦等想,即不會被外境所影響,此即漢語唯識之捨濫留純識之觀,而依應成中觀則生自他想,皆在此義。如《密意疏》云如何除遣世俗人境:「如寶鬘論云:『色法唯名故,虛空亦唯名,無種寧有色,故名亦非有。受想及行識,如大種如我,皆應如是思。故六界無我。』又云:『唯除於假名,若云有云無,世間寧有此。』」漢語唯識學之歷史為西元六、七世紀,而藏語應成中觀之學為西元十三、四世紀,兩者之間傳佈不同,畢竟六、七世紀尚且未有藏語中觀,而藏語應成中觀亦未談及漢語唯識,只需兩者類比即能理解有時所言雖為同一名相,卻所說的卻為不同意義。
以上共勉。
(圖片說明:原高野山真言宗之臺灣總本山 弘法寺,今為台北天后宮之弘法大師 空海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