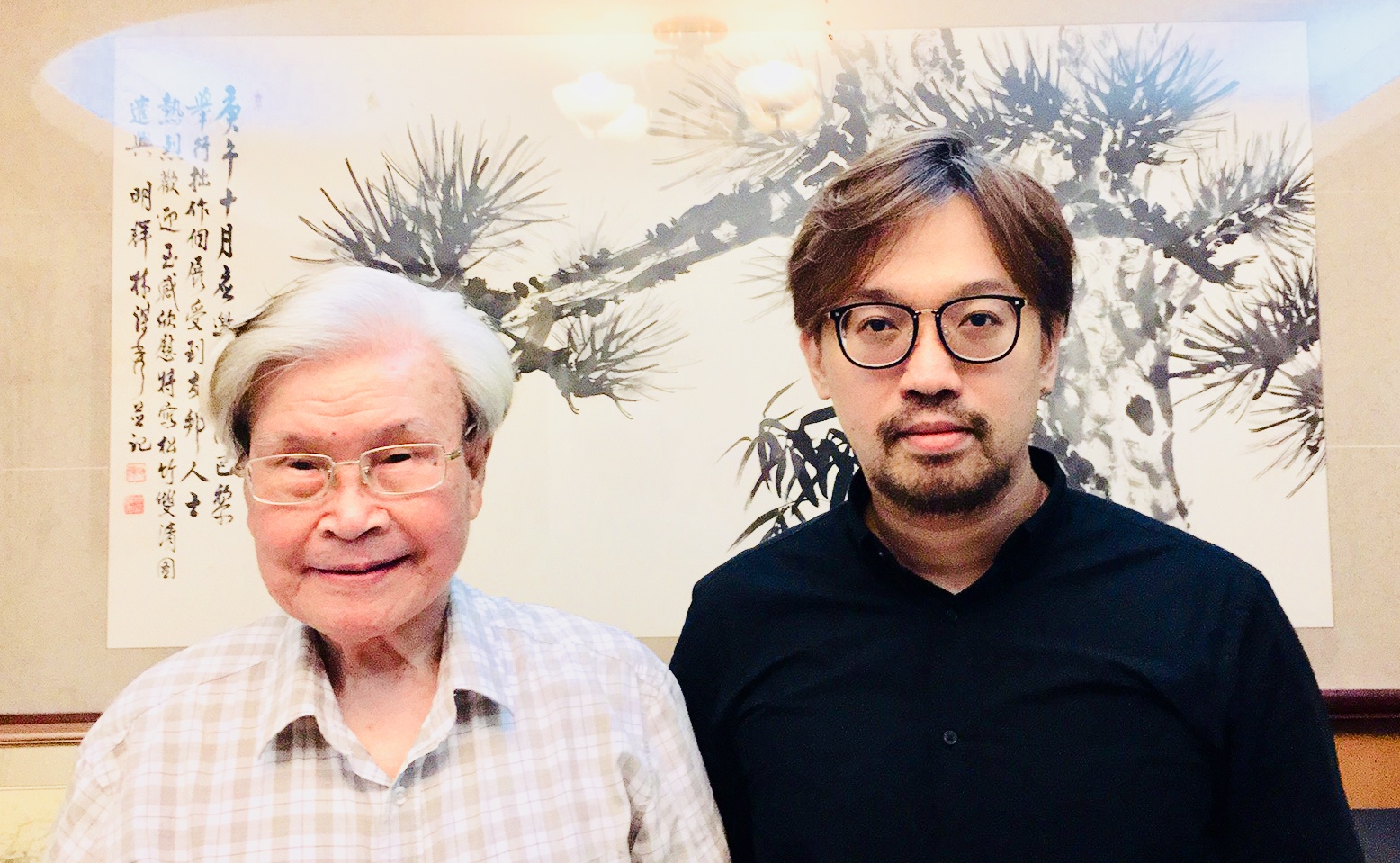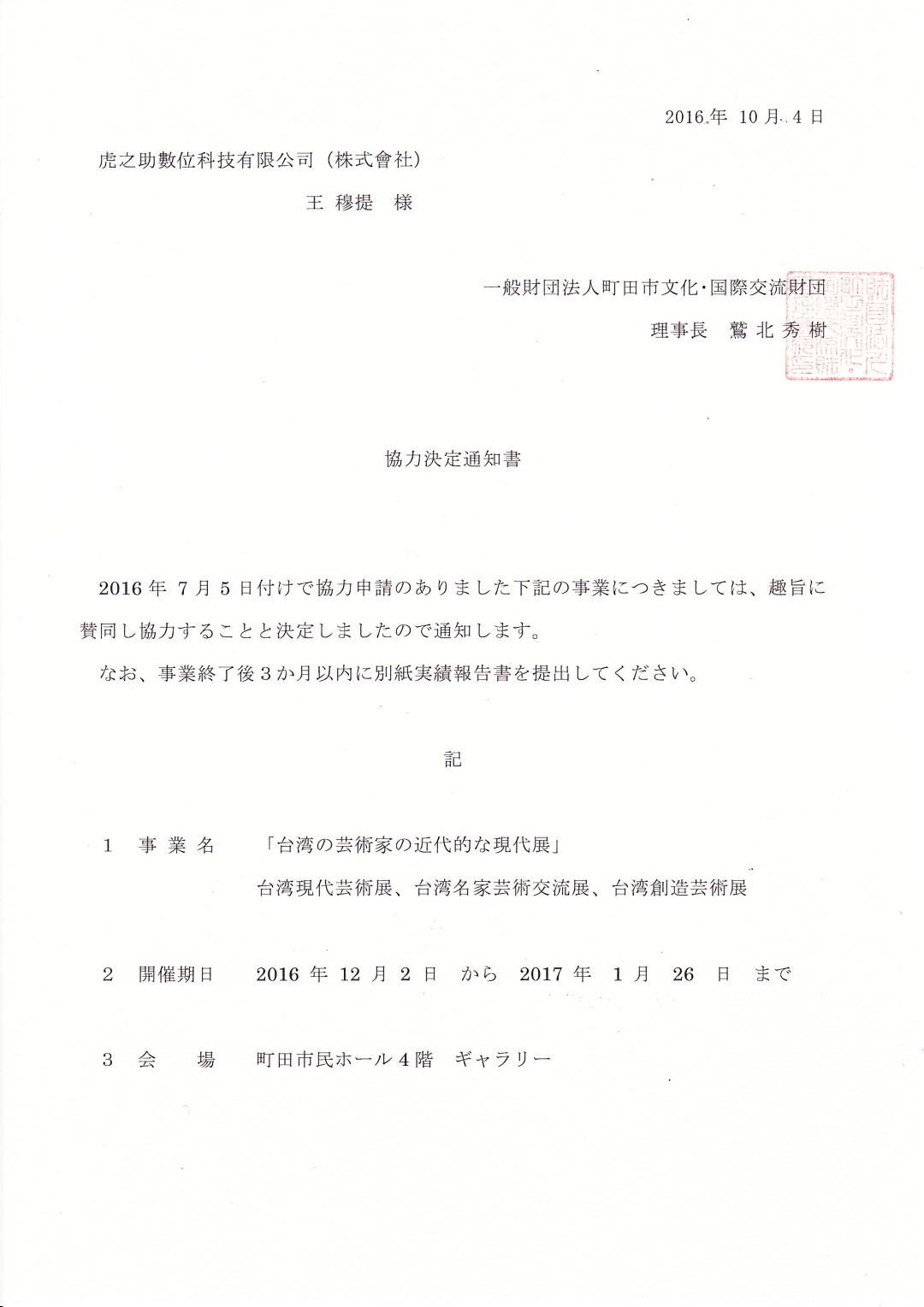「若言無明異於有愛,是亦名為誑於如來。何以故?無明與愛,即是智慧即解脫故。若言三毒異三解脫門,是亦名為誑於如來。何以故?空無相願,即是貪欲瞋恚癡故。」
若言無明、愛等同解脫,亦為法執,執有無明、愛自體故,即有自體如何解脫?以彼無明、愛無自體,即智慧、解脫之故。如下貪欲瞋恚癡亦同此理。
然一分異生見文即言貪欲瞋恚癡即三解脫門,於此貪欲瞋恚癡而做諸有漏行,若無貪欲瞋恚癡,如何能做有漏行?故知彼等於此未明而生執取,進而造諸惡業而不知。無自體故言不異,非執貪欲瞋恚癡而行諸惡行而說不異,既有貪欲瞋恚癡等現行,故說彼等有自體執故,既有所執,如何有不異?
梵谷、高更、塞尚、莫內、畢卡索等作品,日本美術館收藏實力雄厚,雖然普遍為前期作品,然也能培養在日本生活者審美的觀察,藝術品看多了,眼力自然能夠培養。台灣美術館收藏除中國收藏品、近現代台灣藝術家作品外,真正達到世界級的藝術品屈指可數。觀看日本西洋美術館收藏品大抵為日本企業家所捐出或者借展,台灣也有諸多實力雄厚的企業家收藏藝術品,然大多鮮少捐出其收藏品。
有熟識的台灣企業家說等她百年之後,其收藏的張大千、林風眠、傅抱石等作品一律捐給台灣當地的美術館,不留給子女任何一件作品,因為他們不懂畫,拿去轉賣,也只是落到另外一位藏家手裡,不如捐給美術館讓大眾共同欣賞。
致敬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烏克蘭女性藝術家的雕塑作品。現場美術館在說明欄位旁放置募款活動的說明,這在美術館史上鮮少出現這類的人道精神,或許這才是美術與世界的真善美跟上時代的步伐。佛陀說,諸惡莫作,亦即任何的惡,都不應當造作。何謂惡?殺戮即是,任何的殺戮皆是惡,不是分你的殺戮、他的殺戮就是正義,殺戮,即是惡。
法友舉例吃素若是於種植蔬菜時,殺害了更多的生命,如何是功德?其實答案是正確的。吃素不會有功德,如同一個男人見到一個妙齡女子走在路上,正常的男人並不會性騷擾對方,不會性騷擾對方是本來就該做的,如何是功德?這如同受戒者一般,要戒殺,從嘴巴開始。
吃素只能說是消極意義上的戒殺,而不能說是狹義的護生,若種植蔬菜時,加上各種農藥導致周圍之動物死亡,如何是護生?所以最好的辦法即是自然農法,簡單的說,就是與大自然各種動物、昆蟲共存共生,使用純有機物取代農藥,諸如使用辣椒水等噴在農作物上,否則,在超市上看見許多美觀的蔬果,除了溫室栽培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噴了許多農藥,不僅導致土地逐漸失去養分,更會導致更多的蟲死亡,只有人害、哪有蟲害?
見到此文者,又會說,你原來不吃素?非也。本人吃素已經二十八年,然吃素之動機若是追求所謂的功德,實際上是一種邪見,這時又會有人說,那不吃素吃肉好,倘若是受學菩薩戒者,如何能食一切眾生肉而自稱行菩薩道?此等豈非顛倒?菩薩吃眾生肉,如何有淨?再者,現今社會經濟發達之程度,如何有三淨肉?一切工廠皆為提供吃肉者,此等如何說自己為吃淨肉?實在愚癡。
再者,如同提婆達多,提婆達多認為不喝牛奶可以證果,為佛陀所呵斥為邪見,但並非佛陀不禁止喝牛奶,要看情況,諸多律學經書多有說明,這時又有人會說,出家人才能過目律學經書,若如此,編輯大藏經者,多半為在家人,是否違背佛制?若已經違背佛制,是否大藏經亦違背佛制?所以說,這類的言論亦是邪見,有些在家人是隨分隨力持出家戒,所以深入律學,並非於此找缺失。所以說,邪見最為可懼。
取大論卷十三至六十二之文而整理四百問,再配以遁倫《瑜伽師地論記》作解答,於解答中再做種種細問而答之日本 多武峰增賀法師所撰《瑜伽論問答》詮釋人法二無我義,如:「問:經論文處處說補特伽羅空、法空·補特伽羅無我、法無我,何故此空、無我名通人、法俱有乎?
答(云云)問:進云:勞釋文云:空謂所空自性,無我謂無其用及差別義。(文)
意云:空人、法自性俱名空可,然但無用及差別,故名無我可分別。何者?凡云我者,不知蘊、處、界諸法遠離差別義,汎執一合相,總許我也。今此觀諸法遠離差別,知無補特伽羅,卽立補特伽羅無我性也。然空補特伽羅知唯有法時,卽有法執起,空此法執故,但可云法空,不可云法無我。
知唯有法時,無我心起,何空法時云法無我?
答:此義叵思,今聊會釋。觀蘊、處、界諸法遠離差別,便補特伽羅自性都無空,亦觀此諸法空,便法自性空。雖無人、法二性,然有其用、差別,此用、差別卽當我義,故空人、法用及差別,名二無我。
問:何故無用及差別義可名無我?
答:我是自在義,自在起用,自在差別。觀唯有法,雖無我體,然有作業及差別等,卽當彼我自在用義及差別義。今無我體,不空我體,唯空其用及差別等,空用、差別體,名二無我。」
其實,天主教的隱修士亦是吃素的。許多佛教徒並不知道。
根據《元亨釋書》記載增賀略傳:「釋增賀,平安城人,諫議大夫橘恒平之子也。誕質後數月,父母赴東州。於馬上搆轝座,令乳母坐抱兒。一朝早發,乳母抱兒坐馬上,餘睡未寤,放兒落馬。過數里而覺不見兒。乳母悲泣。父母聞之,舉聲哭曰:「若干馬牛,定踏殺我兒乎。雖遺骸,吾尚欲見。」馳歸兒所。狹路中泥土上,兒含笑仰臥。泥水不汙,又無少疪。父母急收,嘆希有焉。其夜,母夢鄉泥土上,有寶床敷天衣。兒臥其上。四天童立四隅,合掌曰:「佛口所生子,我等加衛護。」覺後益珍育。四歲時,初向父母曰:「願上睿山學一乘。」作是語已,又無餘詞。父母驚曰:「嬰孩何作是言。恐是鬼神託言與。」母又夢一時抱兒在懷。忽長大成壯年比丘。手持經卷傍有人曰:「莫恠驚宿,因當作僧。」十歲,父母以初語及夢事,送睿山與慈慧。性聰穎,操履潔。學綜顯密,尤邃止觀。而惡利名絕交謁。安和上皇勑為供奉,佯狂垢汙而逃去。太皇太后敬事為師而延宮中,便於采女中出麁語,又罷去。慈慧任僧正,入宮賀謝,翼從甚盛。賀帶乾魚為劒,乘瘦牸牛,交先驅之列。諸徒叱而去之。賀厲聲曰:「僧正之前馳去,我誰乎。」聽者笑而伏。
天曆二年八月,夢至一所。山川明媚,阿練若僧徒在焉。西南隅,有坦地,見一老翁。首戴青冠,身被赤裘,左手持經,右手携杖。天童神女,左右圍繞。賀問:「誰乎?」對曰:「毗耶離城居士也。住此千餘歲。止此地者,多得佛智。汝盍居乎?」覺後不知何許。應和三年,如覺法師勸上談岑,山川風物,宛如昔夢,因是居焉。四序各修三七日懺,夢南嶽天台諸祖師摩頂曰:「善哉。佛子能勤修行。釋迦、普賢,加護攝受。」常有異人晤語,言涉朝野。以故,雖山中,諳悉京畿之事。州人多來訪問,賀能應不舛。長保五年六月九日,集徒曰:「西方佳期,今其不遠。」即設講莚,談論深旨。又令弟子念佛,自入靜室坐繩牀,誦法華,結金剛印而滅。年八十七。臨終語徒曰:「吾沒不須闍毗,只要窆埋。過三年,開壙見之。」弟子依顧命,作大桶輿,殯寺後。後三年十一月春,秀等啟壙。全身不壞,趺坐儼如也。但衣已朽弊。秀等禮拜讚嘆。
贊曰,浮屠何急乎,清修而已。利源一闢,靡處不至焉。故吾黨貴寡欲矣。源公償五石之費,生師患一山之長。賀老卻供奉之列,三子者吾門清介之士也。今反之,求而不耻用,而不度痛哉。且夫延曆園城之卻,自座主位始。生也同時,彼三千之徒,何不視一生公乎哉。」
增賀之師為良源,如已故聖嚴法師《日韓佛教史》言:「良源於寬和元年(西元九八五年)化去,享壽七十四歲。其門下之盛,堪與孔子與羅什三藏相擬,所謂門徒三千,賢士七十,四哲為最。源信、覺運、尋禪、覺超,號稱四哲。四哲之外,尚有性空、增賀、安海,亦為一時龍象。」
(圖片說明:日本國立西洋美術館致敬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烏克蘭女性藝術家的雕塑作品。)